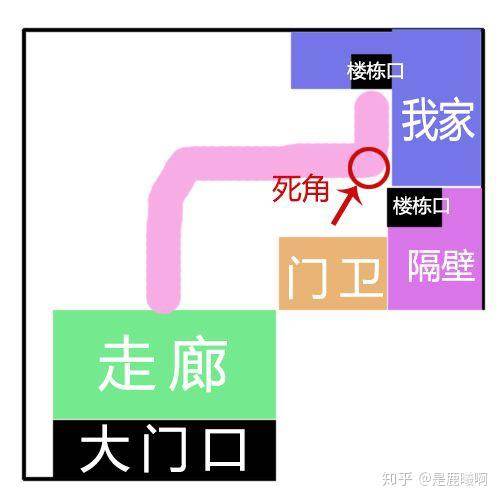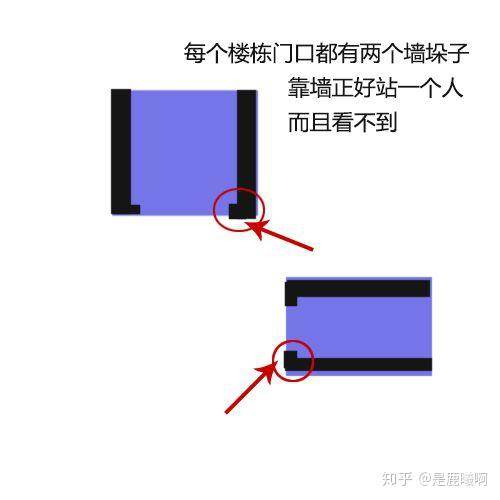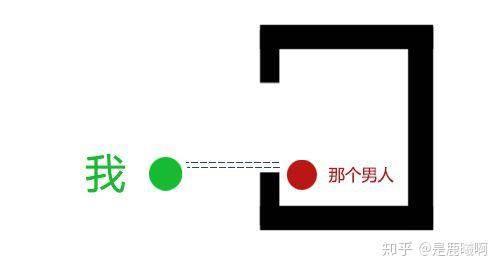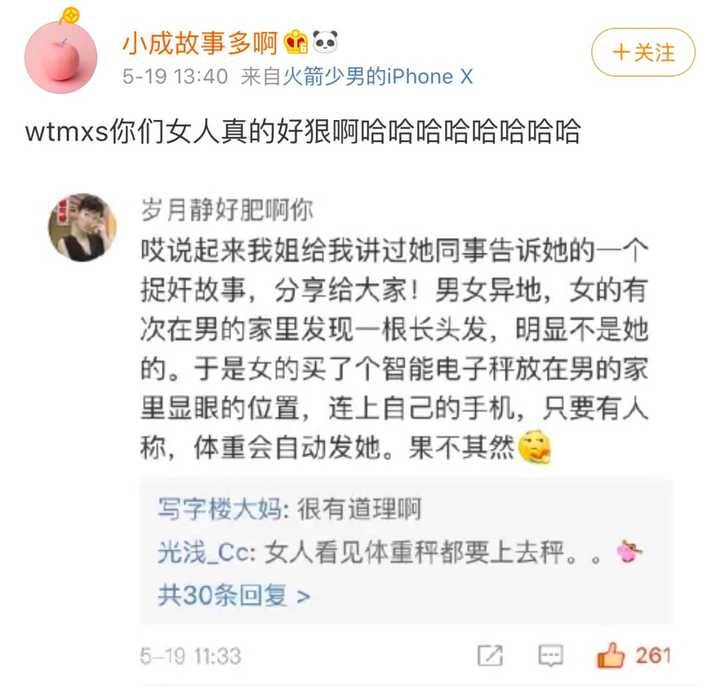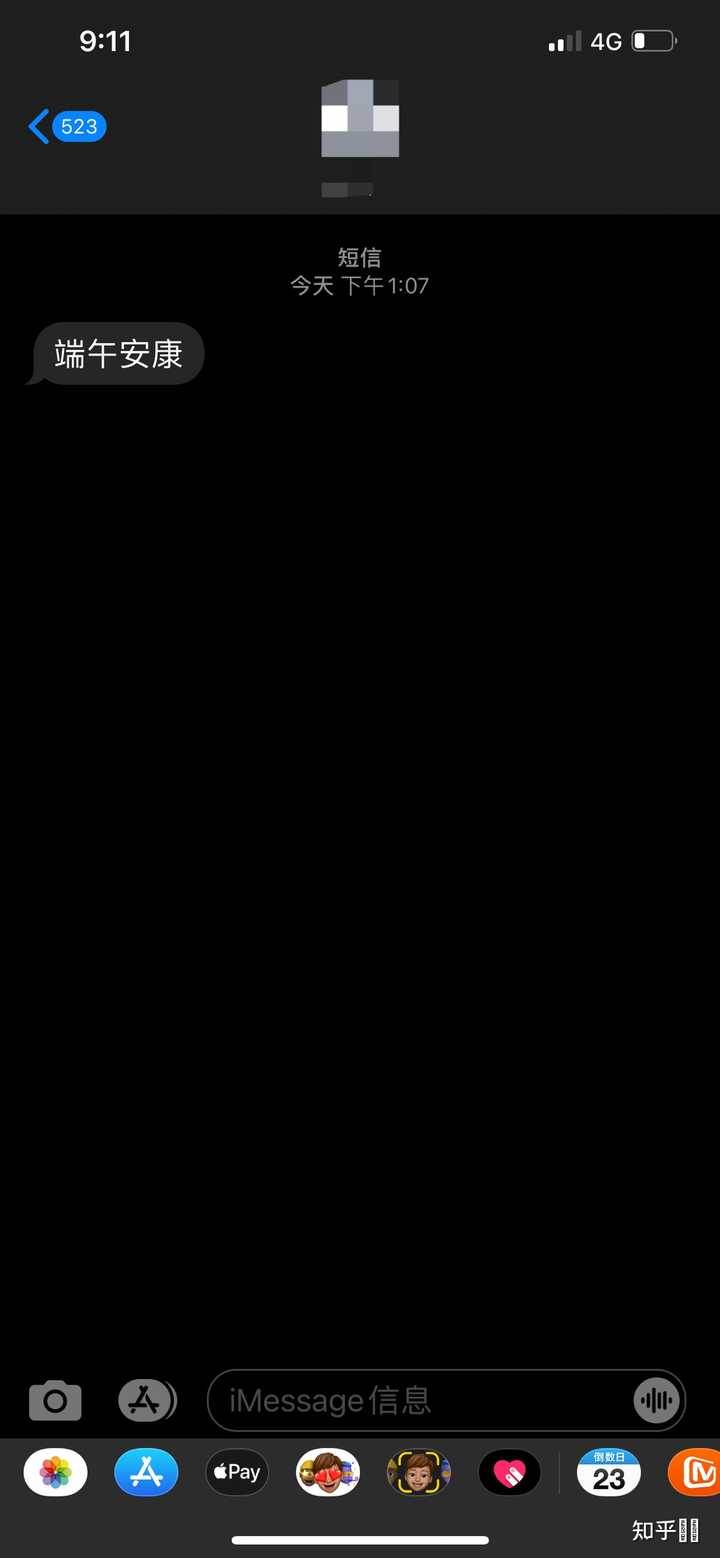我公婆非常看重風水,光是我和男友結婚的日子就選了一年。
沒想到,辦婚禮當天公公暴斃了。
婆家硬說是被我沖撞了,讓我一個人給公公守靈一晚。
我總覺得,他們是借此機會想要把我獻祭給誰。
我和梁紹文戀愛三年多,終于找到機會把婚禮辦了,結果婚禮當天公公死了。
公婆比較信風水玄學,選了很多日子后,終于挑了這一個,領證還要另外看日子。
我家在市區,梁紹文家在縣城,按我們這里的規矩娘家人送嫁后,吃了午宴就要回去的,不能留宿。
所以辦婚禮那天,我爸和我弟將我送到后,吃了午宴就回去了,只留我一個人在梁家。
婚禮是中式的,雖說流程很多講究,新人結婚居然還要去祖墳祭拜。
但兩家都挺盡心,辦得很圓滿。
我公公很開心,喝了很多酒,我爸走的時候,還拉著讓他多喝幾杯再走。
1
送走我娘家親戚后,梁紹文心疼我一夜沒怎麼睡,又穿著厚厚的中式龍鳳褂,還帶著濃妝不舒服,就帶我回新房卸妝換了衣服。
剛將身上的龍鳳褂換下來,梁紹文的叔叔就急急地到了新房外,臉色很難看,尤其是看著我的時候,目光很陰鷙。
但也沒說話,只是朝梁紹文招了招手,示意他出去。
梁紹文的叔叔我也見過幾次,只比我們大十來歲,今年好像都不到四十,性格挺外向的,每次我來都打趣我什麼時候嫁到梁家來。
剛才他那一眼看得我心里很不安,果然等我卸了妝,清點今天得到的改口費和紅包的時候,梁紹文就回來了。
可他就靠在門邊,目光沉沉地打量著我。
「出什麼事了嗎?」我被他看得發毛,卻還是撐著笑問他。
「余心,我爸走了。」梁紹文卻直勾勾地看著我,幽幽地說著。
我當時也沒往那方向想,以為他這是改了口,說的是我爸,當時順口接了一句:「我知道啊,剛才我們一起送走的啊。」
梁紹文臉色卻更難看了,輕聲道:「他喝多了酒,沒醒過來。本家人說是你今天進門沖撞了,讓你今晚給他守靈,等明天再發訃告。」
我正記著紅包數,聽到「沖撞」「守靈」「發喪」這幾個詞后,才知道梁紹文說的是什麼意思。
當下連忙起身:「怎麼回事?」
雖說我不太信這種,可婚禮當天死了公公,怎麼想都不吉利。
午宴的時候,公公還好好的,怎麼一下子就沒了。
梁紹文沒有解釋,只是打量了一眼:「我叔他們已經在布置靈堂了,你換身衣服下來吧。」
這種大事,我是不敢開玩笑的,連忙將身上喜色衣服換了一身素色的長裙。
等我出門的時候,發現外面貼著的囍字,還有金童玉女什麼的,全部都撕了下來。
下了樓,就見原本掛著的紅綢,全部換成了扎花白綢,一具棺材已經擺在了堂屋神龕下面了。
棺材蓋半掩著,我也沒敢看公公是否已經入殮躺在里面了,總感覺他們家辦事速度好快。
梁紹文的叔叔帶著本家人還在布置擺靈,見我下來,個個都臉色陰沉,好像我真的是那種害死公公的禍害。
梁紹文帶我去了旁邊的客廳,就見婆婆臉色陰沉地坐在那里,也沒有哭,只是朝我招了招手:「余心啊,你過來。」
心里很不安,但那些姑嬸都眼神沉沉地看著我,梁紹文拉著我不放手,更甚至將我往后扯了扯,似乎想護著我。
我想著出了這種事情,還是得安慰一下婆婆的,所以反握著他的手,從他身后探頭,正想開口安慰婆婆。
她就瞪著梁紹文要笑不笑地道:「紹文啊,你爸死了,你這是怕我吃了余心嗎?讓她坐到我身邊都不敢?」
那些嬸娘的臉色也不好了起來,靈堂更甚至傳來什麼重重敲打的聲音。
梁紹文身體僵了一下,慢慢松開了緊握著我的手,朝我道:「去吧。」
這氣氛有點凝重,但我想著出了這種事情,也應該的,朝婆婆點了點頭,正要坐過去。
還沒等我坐下,婆婆就拉著我的手,似乎要拉著我坐下來。
可跟著我就感覺手上一涼,就見婆婆把一個很老式的玉鐲套在我手腕上。
那鐲子水頭很好,并不是現在流行的光面,而是雕著龍鳳紋,雕口處還有點暗黃,很明顯有些年頭了。
「委屈你了,這鐲子是梁家祖傳的。你公公的事情,你也知道了,今晚你一個人在靈堂給他守一晚,明天就沒事了。」婆婆還很貼心地拍了拍我的手。
這是讓我一個人守靈?
剛才梁紹文說的時候,我還以為是大家一起守!
忙扭頭去看梁紹文,可他就是看著我手腕上的鐲子,臉色鐵青,脖子上青筋迸現,似乎很生氣。
別看梁家一直在縣城,可家里包了附近所有的山頭,種藥材,開醫藥公司。
從民國初就發家了,家底厚實,家教比較好,梁紹文脾氣溫和有禮,就是比較保守。
談的這三年多,有時我也饞他身子,鬧他,他明明忍得受不了,卻還是沒到最后一步,只是抱著我親了又親,堅持不在婚前圓房。
也從來沒見他發過脾氣,但這會卻惡狠狠的,好像要殺人一樣。
那樣子讓我有點害怕,也有點奇怪,輕喚了一聲:「紹文?」
可他抬眼看向我的時候,眼里盡是陰鷙,還有著恨意?
我本為是他也不同意我一個人守靈,朝他眨了眨眼,想著至少他陪我一起吧。
卻聽到梁紹文道:「這鐲子就不要給她了吧?」
這話說得完全跟我想的不一樣,但確實這種傳家的東西太貴重了,聽梁紹文的意思這鐲子大有來頭。
我忙站起來想取下虛套在手腕上的鐲子,還給婆婆。
想跟梁紹文商量,至少讓他提出跟我一起守靈。
雖說我不怕,但一個人晚上守一晚,也挺那個的。
可婆婆卻一手摁著我,硬是把那鐲子摁在我手腕上,朝梁紹文道:「你爸死了!這鐲子就得歸余心,不管你愿不愿意,這事就這麼定了!」
說著,婆婆朝一邊的二嬸道:「你帶余心去換衣服。」
我聽著莫名其妙,這鐲子歸我,和公公死還有什麼聯系?
難道這鐲子,還是我公公的?
「媽!」梁紹文臉色慘白,一把走過來,拉起我道,「日子你們選的,你們說不會有事,我們才結婚的,現在出了事,怎麼能怪余心。」
我聽著這話,就感覺好像公公的死,還真的是因為我嫁進來。
一時心里也難以接受,轉頭看著婆婆,直接開口道:「要不就讓紹文跟我一起守靈吧。」
公公在婚禮這天死了,這事發生了,也不是爭辯就能讓她們相信跟我沒關系。
以后日子還得過,我也不好新婚當天,把婆家人全部得罪死。
但婚禮是我和梁紹文的,不是我一個人的,他跟我一起守,是應該的吧。
「不行!」結果梁紹文和婆婆同時開口。
梁紹文更甚至吸了口氣,似乎下了什麼決心,朝我道:「余心,你跟二嬸上樓換衣服,我等下就上來。」
可我已經換了一身素色的中式長裙,還換什麼?
二嬸卻努力地擠了個笑,拉著我朝外走,而且她手里還拎著一個顏色黯淡卻很古樸的舊箱子。
她拉著我的手,力氣很大,我想叫梁紹文,她直接就拉著我走了。
等我到樓梯口,回頭看的時候,就見梁紹文好像滿臉怨恨地看著婆婆,而在堂屋布置靈堂的那些本家,都去客廳了。
靈堂這會已經布置好了,可整體布置與我和梁紹文的婚禮差不多,就是沒有貼囍字,把紅綢換成了白綢。
心里有點好奇,怎麼靈堂的東西準備得這麼齊全。
我目光往上掃了一下,就見靈堂擺的并不是公公的遺照,好像是掛的一幅畫。
畫有點發黃,但裝裱得很好。
上面好像是一個頭戴金冠的青年,逆光看不太真切,依稀能感覺出豐神俊朗的模樣。
就在我看過去的時候,感覺手上松松垮垮的玉鐲好像緊了一下,貼著手都有點涼。
可二嬸拉著我走得很快,我連看都沒時間看。
等到了新房,二嬸隨手就將門關了,開箱子的時候,我這才發現,原本被婆婆隨手一套就進去的鐲子,這會好像剛好我手腕大小,怎麼取都取不下來了,我給手上涂了一圈厚厚的乳液都取不下來,反倒把手都弄紅了。
二嬸卻已經從箱子里拿出一身古制的龍鳳褂,與我和梁紹文結婚穿的喜服差不多,可這是純白色的,而且里三件,外三件,一整套。
更甚至還有成套的首飾,但都是銀的、玉的,或是鑲珍珠的。
這一套下來,價值不可估量。
但守個靈而已,用得著這麼……有儀式感嗎?
這東西又是哪里來的?
問二嬸,她只是朝我笑:「就是梁家祖上留下來的,你先去洗把臉,準備換衣服吧。」
我總感覺這事透著古怪,借口要上個廁所,就拿著手機給我媽打了電話。
梁家的意思是要等我守完這一夜靈,明天才發訃告,這會我爸媽也還不知道。
我媽聽著也嚇了一跳,我又把這事的古怪說了,我媽想了想安慰我:「既然這事碰上了,你和紹文想以后好好過日子,就按他家的規矩辦。你婆婆不是還特意給了你個鐲子嗎?估計也是知道委屈你了,他們記著你的情就好。
「你爸和你弟還沒到家,我讓他們馬上回去,問下怎麼回事。就算今晚不在梁家留宿,也在旁邊住著,我現在就叫車去找你!如果今晚怕的話,就讓紹文在門外陪著你。」我媽盡量安慰我。
末了還怕我使性子:「出了這麼大的事情,受點委屈也是應該的,你別怕就行。」
我原本就忐忑的心,也慢慢安穩了下來。
就是看著手上好像尺寸變小的鐲子,感覺有點涼手。
等我出來的時候,二嬸已經將東西都準備好了,婆婆居然還拿著一盒鮮紅得好像口紅的東西站在梳妝台前,說是幫我上妝。
可守靈要上什麼妝?還是用這麼紅的東西上妝?
但現在我一個人在梁家,她們臉上神情都很悲戚,更甚至好像有點害怕?
我想著我媽安慰的話,就按她們的規矩辦吧。
可婆婆說的上妝,卻不是臉。
而是讓我脫了衣服,在我背上畫!
2
我從來沒有聽說過守靈要在背上化妝的,而且還是用這麼鮮紅的東西。
雖然都是女的,可脫光衣服,也不好意思。
所以很明確地表示抗拒:「守靈就不要化妝了吧?」
婆婆卻用手指在那盒鮮紅的東西里攪了攪:「這是雞血和的朱砂,怕你守靈害怕,我在你背上畫道符,這樣就不怕了。」
婆婆信這些,我是知道的,可沒想到她還會畫符。
雖說她這是為了我好,但心頭疑惑很深,我卻還是道:「我打個電話給紹文。」
可婆婆直接拉開了門,就見梁紹文站在門外,臉色依舊陰沉,卻還是勉強地朝我笑了笑:「就按媽說的辦吧。」
我聽得頭都大了,直接一步跨出去,扯著他到外面陽台,問他到底怎麼回事?
他只是不停地告訴我,守完今晚,就什麼事都沒有了,委屈我了,但為了我們以后,一定要守完今晚如何如何的。
他臉上盡是誠懇和苦意,我一時居然有點心軟。
所以還是回房,脫了衣服,讓婆婆用那和了雞血的朱砂在我后背畫了個什麼。
我沒接觸過朱砂,但婆婆那盒子里的東西,有點像那種檀香木才鋸開時的味道,又像是某種花香,但總體來說,很好聞,根本沒有血的味道。
她畫得很細致,也畫了很久,久到我感覺身體都涼了。
畫好后,我原本打算照鏡子看一眼畫的是什麼。
婆婆說看了就不靈了,還拿吹風機給我吹干,這才讓二嬸拿了衣服給我穿上。
這一整套衣服,連里衣都有,等我穿好后,除了一紅一白,其實整體上,和婚禮的龍鳳褂真的差不多。
這成套的首飾更是古樸,看上去居然比我們從婚慶公司定制的更好看。
等弄好這些,就已經傍晚了,婆婆給我端了碗面吃,還和二嬸一起,將新婚鋪著的喜被什麼的,全部換成了白色的,更甚至在床頭還貼了一個白紙剪的「囍」字。
就讓我在房間里等著,說先下去安排一下。
我看著一屋子的白,再看看自己一身白色的龍鳳褂,雖說不信,但還是感覺害怕。
拿著手機給梁紹文打電話,想讓他上來陪我。
可他電話怎麼打都打不通,我給我爸媽打電話,問他們到了沒有。
我爸媽只是告訴我,問了縣城里的人,蔣家似乎祖上傳了這麼個事情。
新婚如果死至親,新娘就得單獨守一晚靈,好像從民國時就有了。
但具體是因為什麼事情,還不知道,但讓我別害怕。
我聽著只感覺離譜,難道他家婚禮當天,經常死至親嗎,還有這種規矩。
還想再問,婆婆和二嬸就進來,說是外面黑了,我可以下去守靈了。
婆婆還要笑不笑地看著我手里的手機:「晚上守靈,手機就不要帶了,免得突然響,嚇到你。」
這話雖沒錯,但我總感覺不安心,所以開口道:「我會調靜音的。
」
婆婆也沒有再說什麼,和二嬸牽著我,下樓去靈堂了。
這會靈堂一個人都沒有了,門口掛著白燈籠,那具棺材的蓋依舊半開著,只能看到里面明黃的墊布,也不知道公公是不是躺在里面了。
我這才想起來,公公死后,我都沒去瞻仰過遺容。
問婆婆,她說讓我別看,免得看了更害怕。
婆婆和二嬸扶著我在棺材前擺著的蒲團跪下,教我燒紙、點燭,和祭香。
而且交代我,無論如何,香火、紙燭都不能斷。
這事情倒是不多,就是有點瘆人,而且我為了婚禮,幾乎一夜沒睡,這又要熬一夜,有點難受。
問梁紹文能不能守在門外,婆婆只是告訴我別害怕,不會有事的,跟著就和二嬸走了,還將靈堂的門給關上了,陰沉沉的靈堂只剩我一下人,越發顯得陰森恐怖。
我跪著一邊燒紙,一邊打量著香燭,眼睛掃過半開的棺材蓋和掛著的那幅畫,越發感覺不像公公,這事越想越奇怪。
但已經到這一步了,也硬著頭皮燒紙。
開始還好,因為害怕,全身緊繃著。
可燒了一會,屋里熱了起來,我一身里三層、外三層的衣服,悶出一身汗,就感覺身體沉重,而且昏昏欲睡。
這種困意,隨著燒紙越來越濃,連害怕都沒了。
我原先還掐著虎口撐一撐,到後來,好像眼皮怎麼都撐不住,連點香燭的時候,看著火光都是晃的。
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時候,靈堂緊閉的門好像被推開了,跟著一個穿著配套白色龍鳳褂的人影走了進來。
我想扭頭看,可實在是困得厲害,跪久了身體也難受,那身衣服才穿的時候感覺精致漂亮,這會汗水濡濕了,就又沉又重。
一轉身,差點被沉重的衣服拖倒了,那人一把就扶住了我,伸手摸著我手腕上的鐲子,一言不發。
屋子里燒得久了,煙霧彌漫的,我眼睛也迷糊得厲害,隱約看著那身衣服,與自己身上的配套。
瞇眼想看他的臉,卻怎麼也看不清,隱約感覺很熟悉。
以為是梁紹文忙完外面的,進來找我了。
輕喚了一聲:「紹文?」
那人輕笑著應了一聲,手在鐲子上摩挲著,摟著我的手緊了緊,將我拉到懷里,沉聲道:「新婚夜?」
那語氣好像并不是很高興,還有點生氣。
還在我脖子上嗅了嗅:「你用犀角香了。」
他聲音低醇,和梁紹文的聲音不太像,可卻很好聽。
我實在是困得不行,努力瞇眼看著他,可火盆前煙熏火燎的,眼睛熏得連衣服上的龍鳳紋都看不清了,更別說看到長相了,但那種熟悉感讓我很安心。
雖然心底擔心梁家人發現他偷溜進來,可實在太困了,伸手圈著他的腰,靠在他懷里:「我瞇五分鐘,你幫我燒會,再叫醒我。」
接著就要閉眼,但他似乎很開心了,摟著我往懷里拉了拉,幾乎將我整個抱起來,貼在我耳邊輕聲道:「這就睡了?」
我困得眼皮都打架,含糊不清地「嗯」了一聲,就感覺唇上一涼。
跟著就聽到他貼著我,輕聲笑道:「新婚夜呢。」
這次語氣中,盡是愉悅。
梁紹文以前很克制,每次鬧騰一會,都強忍著跟我說,等我們辦了婚禮,就有我好受的。
我以為是他特意摸進來,可這畢竟是靈堂,伸手推了推他:「別鬧。」
但他手卻靈活地鉆進了這里三層、外三層的衣服里。
我掙扎著想睜開眼,可好像身體發著軟,靠在他懷里,怎麼也睜不開,迷迷糊糊的,似乎后背一陣陣地發熱。
過了一會,沾著汗水,沉悶的衣服被脫下來,他抱著我躺了下來,我跪得酸軟的身體,躺平后,舒服得輕嗯了一聲,惹得他一陣陣低笑。
更甚至體貼地幫我揉著腰腿,卻朝我喃喃地道:「我等你很久了,你就只想睡嗎?」
我實在迷糊得厲害,想著他都這麼體貼了,伸手勾著他脖子,表示了一下安慰。
就這一下,我就感覺整個不一樣了,撫在膝蓋上幫我揉著的手,好像慢慢地加大了力度。
后面就一發不可收拾,我最后一點意識告訴自己,現在不太合適。
有時睜開眼,迷迷糊糊地好像有著長長的黑髮在眼前垂晃,但整個人好像從背后發著熱。
好像連困意都沒有了,只是有點迷糊地隨著他癲狂。
隱約想著,果然忍了這麼久啊……
最后,我實在困得不行,不知道是跪久了全身酸軟呢,還是其他原因。
就算沒了那里三層、外三層的衣服,汗依舊不停地流。
可他還是不知饜足,我推了他幾次,說累了,他卻一直哄我。
到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睡過去的。
只是感覺他不停地親著我,在我耳邊低喃著:「我等你很久很久了。
」
「嗯,知道了。」我以為他是說這三年,推了他一把,「記得幫我去靈堂燒紙。」
他好像悶悶地笑了一聲,跟著緊摟著我,輕應了一聲:「好。」
我是被雞叫吵醒的,一聲接一聲的雞鳴,好像扯著嗓子叫一樣,而且明顯很多只。
但實在太困了,我努力想睜眼,卻還是睜不開。
迷糊間,又被親了兩口,他似乎摟著我依依不舍。
但雞叫似乎越來越厲害,一聲接一聲,連個空閑都沒有。
隱約還有著門被推開的聲音,并不是房間門用的消音鎖,而是那種大門推開的聲音。
我聽得一個激靈,猛地想起自己還在靈堂。
連忙睜開眼,入眼卻是一片黃澄澄的布,感覺有點熟悉。
伸手摸著這布,有點滑,不太像床單,而且好像還很窄,側躺著所見的地方整個都是這種明黃……
我順著這「床單」翻了個身,入眼就是一方窄小的空間,頭上還半垂著一個白綢扎花,以及半截黑沉的木頭……
猛地想起這是什麼!
我直接一個打挺想坐起來,卻發現腰腿酸軟,身上除了蓋了一件袍子,什麼都沒有穿。
跟著梁紹文就出現在棺材邊,見我躺在里面,似乎也嚇得臉色青白。
連忙伸手將半蓋著的棺材蓋推開,裹著衣服將我抱了起來。
我這會嚇得整個人都蒙了,不停地喘著氣,想尖叫,卻叫不出來,只是緊緊揪著裹在身上的外袍。
更別說問梁紹文,這是怎麼回事了。
但他抱我出來的時候,我發現自己身上穿的那些衣服、首飾,就掉落在棺材旁邊,也就是說,昨晚就是在這脫的。
梁紹文看著這些脫落的衣服,臉色發青,直接抱著我上了樓。
我這才發現,靈堂的門雖然開過,可進來的好像只有梁紹文。
門這會又關上了,可雞卻依舊扯著嗓子不停地叫。
我完全被嚇醒了,扯著梁紹文顫抖地道:「昨晚……」
「是我!」梁紹文低頭看了我一眼,下巴繃得緊緊的,「是我把你抱進棺材里的。」
他這回答,很奇怪。
就算梁紹文膽子再大,和公公再沒感情,要和我補新婚夜,摸進了靈堂,也得偷偷抱我回婚房吧?
在棺材里?
他信,我都不信!
我不由得扭頭看了一眼下面的靈堂,卻見那幅掛在靈堂的畫,突然「啪」的一下,掉了下來。
梁紹文腳下也是一頓,扭頭看了一眼,整個人都是僵的。
3
在畫像掉下來后,梁紹文和我都被嚇到了,他抱著我,幾乎一步兩個台階,噌噌地上了樓。
而雞鳴不斷,靈堂的門卻依舊緊閉著,婆婆她們沒有一個人進來的。
梁紹文將我放在床上,不知道是累的還是什麼的,臉色鐵青,喘著氣道:「雞叫就算一晚了,我去把你衣服拿回來。」
跟著就急急地就走了,估計是怕別人發現靈堂的異樣吧。
我這會回過神來了,趁著沒人,將裹著的外袍脫了,直接跑到廁所,對著洗漱台的鏡子,想看下婆婆到底在我后背畫了什麼。
等我看的時候,除了一身紅青的吻痕,后背上什麼都沒有。
但昨晚,后背一直髮熱,就像貼著好幾個暖寶寶一樣。
正看著,外面梁紹文又回來了,敲著廁所的門:「余心,你在洗澡嗎?」
我看著鏡子里,自己什麼都沒有穿的身體,抬手想裹著浴巾,卻發現那只鐲子依舊好好地套在自己手上。
想起昨晚那個人,一下下地撫摸著這鐲子的事情,我心頭一陣陣發寒。
那人絕對不是梁紹文!
可他為什麼承認?
對于這種事情,是個男的不都該零容忍嗎?
使用 App 查看完整內容
目前,該付費內容的完整版僅支持在 App 中查看
??App 內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