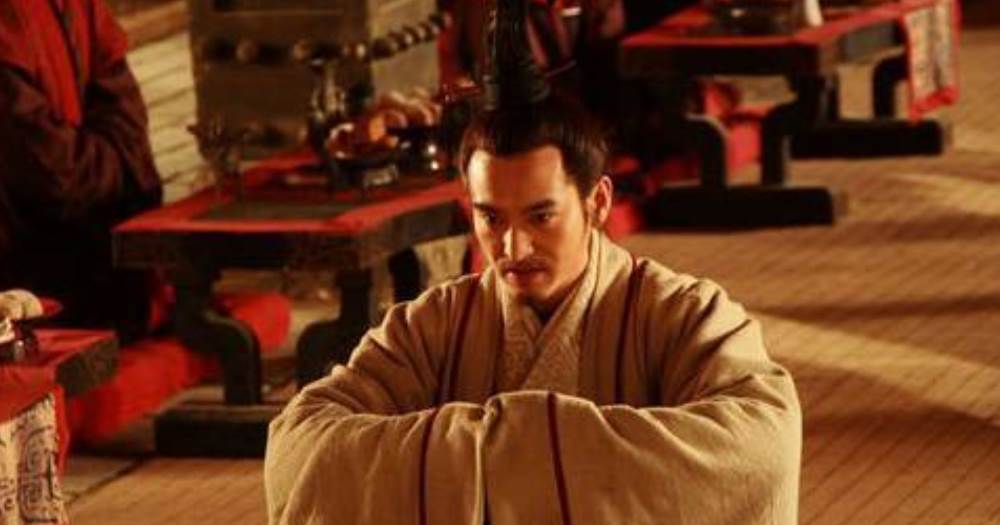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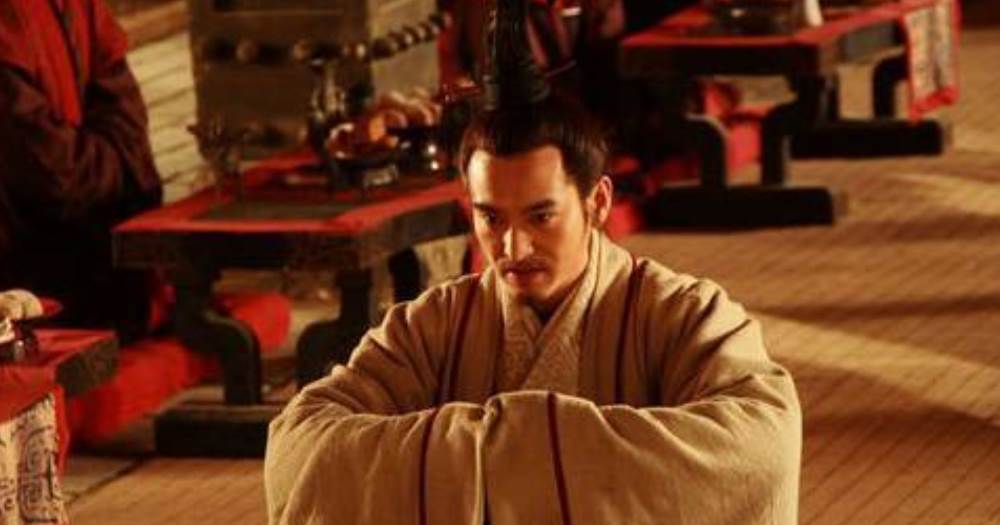
首先應該承認,齊王建能夠穩穩當當坐齊王位置長達43年(前264-221年),他的智商是在正常范圍內的。
其次,秦國想統一天下,統一天下需要滅掉所有國家,其中也包括齊國。只不過因為齊國和秦國不接壤而且距離遙遠,作為權宜之計,秦國選擇暫時和齊國交好,等到秦國把其他國家都滅掉,它最后還是會來滅齊國。這一點應該不難看出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也越來越容易被看出來。
既然齊王建智商正常,來自秦國的威脅也容易看出來,那他應該清楚,其他國家是齊國的外圍屏隔,這些屏障如果不存在,齊國自己也在劫難逃。那麼,他為什麼直到最后都不去援助這些抗秦國家呢?
這確實是個令人迷惑的問題。
下面提出我的觀點,這一現象的背后原因在中國歷史上并不罕見,歷朝歷代反復出現過。
說來話長,當初,齊國政權是田氏從姜氏手里纂奪得到的,奪權之后,田氏開始總結姜氏失敗的經驗教訓,它認為,姜氏犯下的根本錯誤在于:不信任本族人,重用了像田氏這樣的外族人。
為了不重蹈姜氏的覆轍,為了鞏固新政權,田氏決定反其道而行之,它只重用本族人,同時,它還不擇手段迅速擴大本族人數量,出台政策鼓勵所有族人多生養后代,姓田的人越多,它才覺得越放心。
比如,田常為相時,他選擇七尺以上女子入后宮,嬪妃數以百計,而他的賓客和舍人出入后宮不禁。
等他去世,有子七十多人。
他的兒子田襄子盤把全國八十多個縣的長官全換成他的兄弟和田氏族人。
時間長了之后,這種政策造成的結果是,田氏族人幾乎無處不在,遍布齊國各地,宗室力量異常強大。
從齊威王后期到齊宣王時期,再到齊閔王前期,作為宗室代表的靖郭君田嬰,孟嘗君田文父子相繼為相數十年,連齊王也需要尊重他們的意見。齊閔王無法容忍權力分散,他決心扳倒孟嘗君,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靠了些運氣他終于成功,開始獨掌大權。
齊閔王結束了齊國的傳統國策,然而,他的替代政策卻是:重用外國使臣。來自燕國的蘇秦,來自秦國的呂禮,來自韓國的韓珉(韓聶)都曾經在齊閔王手下為相。
齊閔王忘了一件事,如果你連自家人都不相信,其他人不是更不能信嗎?扳倒孟嘗君之后,齊閔王新政策推行僅僅十年(前294-284年),他就把齊國搞得差點滅亡。
當時強大無比的,秦國遇到都要退避三舍的齊國是怎麼被齊閔王稀里糊涂帶進泥坑里的?燕昭王可以隨意玩弄他,還派了個蘇秦當面忽悠他,讓他犯下吞并宋國的戰略錯誤,從而引發五國伐齊。
在五國伐齊戰爭中,他先是瞎指揮,然后又不指揮。他先是顯得過于樂觀和自信,命令齊軍集中起來和聯軍決戰。後來只剩下燕國攻齊的時候,他又無法擺脫失敗情緒的影響,顯得過于悲觀,國家正處于崩潰邊緣,他卻完全不管不顧,放棄了組織抵抗的基本職責,自己跑到國外的衛國,魯國和鄒國去躲避,這些小國都看不起他,把他趕出來,他這才被迫回到齊國的莒城。
他記吃不記打,回到莒城后,他又任命一個外國人-楚國人淖齒為相,允許楚軍進駐。既然他自己送上門來,淖齒也不客氣,趁其不備動武占領莒城,對他下了殺手,他最后死得很慘。
他的政治生涯直接變成一個個笑話在國際間四處傳播,人們津津樂道,他也因此榮膺昏君的代名詞。
他的表現極其,極其糟糕,以至于拉低了齊國王室的形象,聲望和權威,畢竟,此后的齊王都是他的后代。
齊國人和秦國人性格不同。秦國人特別順從,無論是誰,只要手握權力,秦國人就會對他唯唯聽命。齊國人有很強的獨立意識和自主性,在他們看來,著名笨蛋齊閔王的后代不會有多聰明,政策也不會有多高明,憑啥服從?他們經常不聽話,唱反調,齊王感覺統治不穩固,憂心忡忡。
齊閔王的兒子齊襄王全程目睹父親的經歷和結局,他的心靈難以承受猛烈沖擊,留下嚴重創傷,再也沒有恢復常態。
莒城被楚軍占領,齊王被殺,中央政府覆滅,這個時候齊國己經可以正式宣布死亡了。
也是在這個關鍵時候,有個叫王孫賈的人迅速站出來,在他的鼓動下,當地人紛份起來反抗,消滅楚軍,殺死淖齒,收復莒城,重建政府,齊國驚險地起死回生。
在此期間,齊襄王做了什麼?事變剛發生他就找一個偏僻地方躲藏,心思都用在和君王后談戀愛上,對外部事務充耳不聞。他躲得很嚴實,其他人重新控制莒城之后到處尋找,找了很久才把他找出來。
齊襄王給人的感覺是失去了方向感和希望,只剩下聽天由命和麻木不仁。
後來,田單在即墨城創造了奇跡,他用火牛計大敗燕軍主力,又從即墨出發風卷殘云般連下七十余城,恢復了齊國的基本盤。同時期,齊襄王有沒有搭順風車,從莒城出發恢復幾個城池呢?沒聽說過。
齊襄王毫無作為也是因為齊閔王的教訓。齊閔王這個人積極有為,總是在忙著做各種事,而且總想做大事,事后卻發現,他做的越多錯的越多,事情越大傷害越大。
齊襄王認為自己的資質比齊閔王強不了多少,齊閔王接手的齊國處于鼎盛時期,可是也經不住他瞎折騰,犯錯誤。自己接手的齊國弱得多,不能再折騰,再犯錯了。想來想去,他決定--躺平,干脆什麼事也不做。不做事不會有任何貢獻,但是,至少可以避免象齊閔王一樣犯錯。
齊襄王的行事準則就是什麼事也不做,他的行事準則被齊王建繼承下來,整個戰國后期六十年時間里,齊國奉行的都是這個行事準則。
同樣在戰國后期,穓下學官里有一個叫黃老道家的學派異軍突起,興盛一時,它應該是得到了金主齊王的大力支助。黃老道家主張「無為而治」,齊王用黃老道家來論證他「什麼事也不做」的政治路線是對的。
四。
我們再來想象一下樂毅率領燕軍進攻齊國時候的情景。
一邊,樂毅在高歌猛進,另一邊,原本分布在齊國各地的田氏族人紛紛向著那些還沒有被燕軍占領的地方遷徙,田單就是其中一個。
當齊國地盤只剩下莒城和即墨兩個城池的時候,來自全國的田氏族人都遷徙到這里,這兩個城池里逐漸匯集起大量同族,有血緣關系做紐帶,他們團結一心,眾志成城,這兩個城池變成難以攻克的硬骨頭,齊國最后的堡壘。
為什麼騎劫一說要挖墳,整個即墨城都群情激憤?他挖的應該是田氏宗族的祖墳。
田單是田氏宗族推舉出來的領頭人,他指揮的軍隊,各級軍官主要都是由田氏族人充任。所以,田單復齊不是田單一個人創造的天才奇跡,而是田氏宗族的絕地反擊,是在即墨避難的田氏宗族成員集體奮斗的成果。
從王孫賈名字來看,他的身份是一個宗室貴族。
他在莒城振臂一呼就能獲得群起響應,響應他的應該也是田氏族人。
這些是史書中留下明確記載的事件,還有一些事件沒有記載在史書中,但是可以間接推斷出來。
五國伐齊的時候,齊軍和聯軍在濟西決戰,齊軍遭遇慘敗。接下來,孟嘗君使出渾身解數,想辦法擋住,或者勸退了五國里的四國,只有燕國他沒能擋住,于是我們看到,五國伐齊突然變成只剩下一個燕國在繼續攻齊,齊國面臨的壓力大大減少。
五國伐齊之后,燕國和趙魏兩國結成三國聯盟,前284年到前279年,這五年時間里燕國和趙魏都是盟友關系。魏國大梁遭到秦軍進攻,燕國兩次出兵助戰,它履行了盟友義務。然而,燕國連續五年猛攻莒城,即墨不下,趙魏卻從來沒有出兵給燕國助戰,一次都沒有。
田單起勢的時候燕國兵敗如山倒,只要不傻,這個時候它肯定會向兩個盟友緊急求援,然而,趙魏卻巋然不動,眼睜睜地看著燕國勢力被徹底趕出齊國。
一種不合常理的現象如果只是偶爾出現,還可以說是巧合,但是,它在長達五年時間里反復出現,那它應該就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刻意所為。
身為趙,魏,燕三國聯盟的領袖,孟嘗君一直在暗中運用自己的影響力,阻撓趙魏出兵支援燕國。
他的正式身份是魏相,明面上他必須根據魏國的利益行動,不能根據齊國的利益行動,他給齊國提供保護只能在背地里悄悄進行,史書中因而沒有留下相關記載。
總結下來,從五國伐齊到田單復齊,齊國在最危險關頭保住一線命脈,後來還成功復國,真正原因是國內外田氏族人為了救齊國共同付出的努力。
田氏宗族在復國過程中起到了中堅作用,當時與論普遍認為,對宗族以外的人而言,受齊國政府還是燕國政府統治無所謂,國家危難時刻仍然忠誠于齊國的,能夠信賴和依靠的只有宗族成員。
不難理解,數量眾多的宗族成員傾向于支持田嬰,田文之類宗室貴族代表他們利益在中央執政。
齊襄王發現,社會上回到以前傳統國策的呼聲很響亮,宗室對政治的影響大有卷土重來之勢。
齊閔王好不容易才把宗室打壓下去,齊襄王不想放棄這一寶貴成果,但是齊閔王重用外國使臣的政策顯然行不通。怎麼辦呢?齊襄王的選擇是走第三條路--扶持外戚,以君王后和后勝為代表的外戚集團開始在政壇崛起。
齊軍主力部隊的絕大部分是在田單連下七十余城,直抵燕國邊境的過程中組建起來,如前所述,田單手下各級軍官和骨干力量都是田氏族人。
自然而然地,宗族在軍隊中枝連脈結,扎根很深,軍隊被經營成田氏宗族的后花園。
為了遏制宗室的發展,就必須遏制軍隊的影響力擴張。打仗依賴軍隊,為了遏制軍隊的影響力擴張,就必須少打仗或者不打仗。
「齊閔王后遺癥」深深困擾著齊國王室,他們對自己的指揮能力毫無信心。一旦與外國發生大規模戰爭,他們覺得到時候自己很可能又會表現得很笨拙,又犯錯誤,吃敗仗,本來就偏低的權威又一次受創。然后,又有某個能干的田氏族人出來撥亂反正,力挽狂瀾,就象田單一樣。
此類事件反復發生,王室的面子還要不要?宗室還能不能遏制住?
與其到時候頭疼,不如從一開始就杜絕此類事件發生,不讓軍隊有顯示重要性的機會,不讓王室以外的田氏有表現的機會。所以,戰國后期的齊國變成縮頭烏龜,它不僅閉關自守,盡可能不參與國際紛爭,甚至連別人打了它都忍氣吞聲不還手。
俗話說:「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如果你身邊有一個人軟弱可欺,你給了他幾拳他不還手,你會有什麼反應?居然有這種好事,那我繼續打,隨便打啊。別人看到也跟著打,百拳就朝著這個人來了。
燕昭王之前的燕國也從不想惹事,實施閉關自守傳統國策,但是別人先打它之后它還是會還手的,它知道不能什麼事都不做,必須以牙還牙報復回去。齊國是真的不還手,那它怎麼防止百拳來呢?
它把希望寄托在秦國身上,周邊鄰國(趙,魏,楚)打齊國最方便,齊國擔心它們打上癮。它認為,秦國進攻這些國家對它有利,而且攻勢越猛烈越好。這些國家必須全力應對秦國,它們就抽不出手來打齊國。
齊國還高調地和秦國搞好關系,制造一種潛在威懾。它可以放話,誰敢欺負我,我就請求好朋友秦國替我出頭,后果自己惦量吧。
理論上講,整個齊國都屬于齊王,國家利益和齊王的個人利益應該是吻合的。然而,千姿百態的現實往往比理論模型要復雜得多,齊王經常感覺到,他的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不完全吻合。
兩者發生沖突的時候,齊王會怎麼選擇呢?人性都是自私的,齊王也不例外。他選擇堅決維護自己的利益,而把國家利益犧牲掉。
在國家最需要他的時候,齊閔王選擇跑到國外去保命,在他眼里,自己的小命比整個國家的存亡都更重要。
君王后,后勝這些外戚沒有聲望,沒有資歷,沒有功勞,沒有才能,無論從哪個方面看,他們的水平比田嬰,田文,田單差遠了,他們上位純粹是依靠和齊王的裙帶關系。讓沒水平的人治國理政不僅效果差,亂世當中風險也大,但齊王就是選擇在長達幾十年時間里都賦予他們大權。
他們沒水平對齊王來說可能是一種優點,因為不會襯托出齊王自身也相當一般的水平。在孟嘗君的襯托下,齊閔王顯得很蠢;在田單的襯托下,齊襄王顯得很無能。齊王也是有自尊的,外戚用著輕松,舒服,順心,這就足夠了。
田單認識到這個問題,他的耀眼成就反襯出齊襄王的黯淡無光,齊襄王嘴上不說但心里很不高興。
為了自保,田單開始實行韜誨之術。眼看著他就要收復所有齊國縣城,把燕軍徹底趕出齊國,這個時候,他故意留下一個城池不收復,幾年都頓兵城下,做出無力攻克的樣子。當時田單的威名正如日中天,他自己貶損自己的威名,讓齊襄王心理平衡一點,他就可以安全一點。
趙攻齊,取高唐,平邑,饒安;魏攻齊,取平陸;楚攻齊,取南陽之地。齊國五都丟了兩個(高唐,平陸),齊王還是很鎮定地把軍隊摁住不準出動,他確實達到了少打仗或者不打仗的目的,但是,軍隊不出動意味著領土丟了就丟了,收不回來,國家吃虧了。
歷史發展到某個時間點上,秦統一天下的趨勢已經再明顯不過。比如前230年韓國滅亡,其他國家也在秦國的進攻下岌岌可危,朝不保夕。這個時候,秦國的野心是人都看得出來,是人都知道秦國的目標是橫掃六國,每一個獨立國家都受到來自秦國的致命威脅。
按理,這個時候齊國總該出手自救了吧?還是沒有,它坐視各國一一覆滅,最后僅剩下自己孤立無援,只好投降。
齊王想的是,如果他出手,等于默認此前幾十年齊國的基本路線都是錯誤的,是目光短淺,養虎遺患之舉,也會給人抨擊他的把柄,不能開這個口子。
直到齊國滅亡為止,齊王都態度強硬地堅持己見。他是最高領導,想耍賴別人也拿他沒辦法。
對錯不重要,重要的是齊王權威不容置疑,齊王不能認錯,架子不能倒。
但是,國家利益又一次躺槍,如果齊國去支援其他正在抵抗的國家,它應該能夠多存活一段時間。
大家可能覺得齊王的舉動很怪異,難以理解。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這種事情太常見了,幾乎遍地都是,一點不奇怪。
我們經常不明白某個皇帝為啥倔得很,腦袋里面少根弦,明明政策不咋地,他卻一定要堅持到底,直至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最后還是國家買單,人民受難。
比如安史之亂前的唐玄宗,靖康之變前的宋徽宗。
這是因為我們習慣從國家利益角度判斷政策好壞,如果換一個角度,換成皇帝個人利益,你會發現,他們己經考慮得非常周全,滴水不漏,現有政策簡直就是最佳政策。
皇帝也是普通人,不是大公無私的圣徒,你說的再有道理,觸及他們的利益也會白費功夫。
齊國的情況是因為它身處兇險亂世,亂世當中,政策一旦出問題,它的危害會被放大,凸顯出來,讓我們清楚看到,僅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