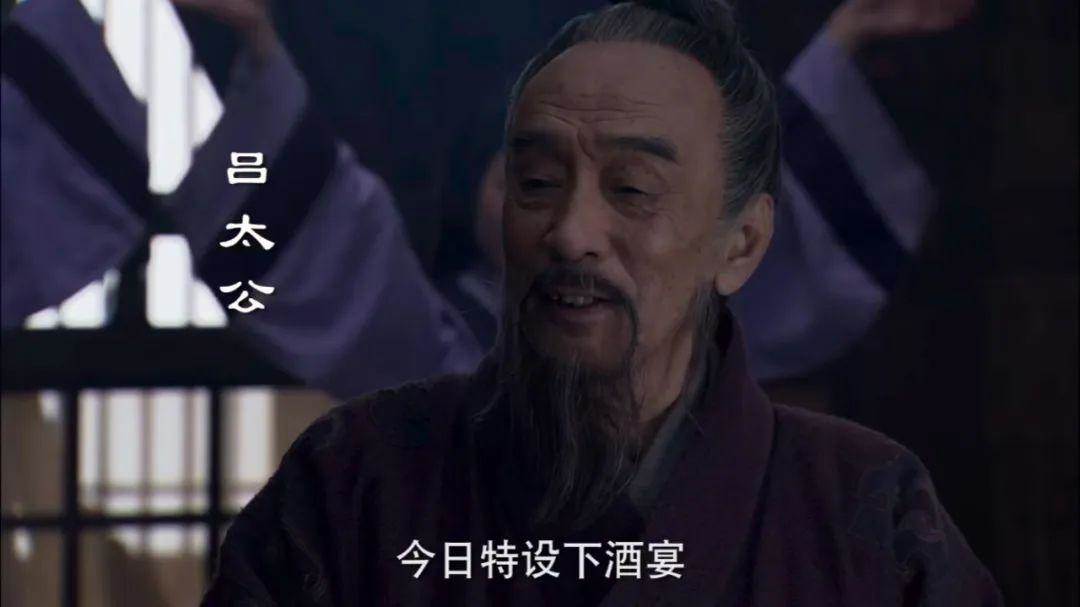謝邀!
先說結論:呂公初次見面便因「面相非凡」而把女兒許給了劉邦(那時還叫劉季)這件事,大機率是小說式的離奇故事。
正史的一個寫作原則是「為尊者諱」,即對掌權者尤其是帝王的行為進行文過飾非的處理。
這意味著,正史對于帝王的貶損基本是可信的,如果不是實錘,有且僅有一顆腦袋的史官絕不敢寫,而對于帝王的褒揚,就要多個心眼了,尤其要警惕史官想誘導人們得出的那些結論。
像呂公初次見面便把寶貝女兒許給了「面相非凡」的劉邦,史官寫這件事想告訴我們什麼?
劉邦的面相就帶著大富大貴,龍鳳之姿啊,天日之表啊,總之就是注定要做天子的人。
我們今天當然不會相信這種敘事。而且,這個故事如果是司馬遷寫的,以他的見識,恐怕也不信,只是不得不那麼寫而已。
他要是把本朝太祖高皇帝的平民時代寫成多數人所過的那種稀松平常的日子,不突出一下他生來注定、天命所歸的過人之處,那繼承了高皇帝基業的武帝們能答應嘛?
對于司馬遷們來說,故事還是要編的。就算這件事是高皇帝自己親口說的,他也不能只是記下來,而要發揮文學特長加工一下,把事情寫得繪聲繪色才是!
對于我們來說,怎麼看這個故事,怎麼覺得它違背常識、常理和常情!
首先,面相這種事我們是不信的,這個就不用多說了。
其次,有哪個父親會把親生女兒許配給自己剛剛認識的人?更別說這人不怎麼年輕,風評并不算好,還窮得叮當響以至于酒錢都經常欠賬?呂公又沒帶著呂雉去做了DNA檢測,然后拿著檢測報告出來后一臉黑線……
再次,即使呂公真是相面達人,真心覺得劉邦面相貴不可言,那也不止嫁女兒一種結交方式吧?套近乎、哈啤酒、給贊助、拜把子……這些方式不也管用嘛?更別說劉季真的缺錢,給錢肯定管用,更別說外黃的張耳沒搬到沛縣,更沒嫁女兒,也和劉邦處得很好!
所以,初見面即嫁女基本不可信。那麼,真相是什麼?
這個沒有足夠硬的史料,只能結合各種蛛絲馬跡推理。

外來戶呂公和本地土著劉邦首先需要相識。縣府約飯這茬,起的作用應該是二人第一次相見并相識。
那天來的都是頭面人物,富戶、官吏、各條戰線上的「豪杰」人物……劉邦亭長為何偏偏能在一幫本縣精英中脫穎而出被呂公捕捉到?
這就要說劉邦詐捐一萬錢、窮人坐堂上了,這就要說劉邦一來就先聲奪人,一坐就談笑自諾了,這就要說劉邦慢而侮人了,各種戲弄取笑別人了,這就要說劉邦輕松駕馭酒桌政治,搞得自己好像男一號了……
總之,呂公成功地注意到了劉邦!他覺得這人雖說只是泗水亭長,兜兜里也木錢,一開口便罵罵咧咧,但是人說話挺逗的,性格挺討人喜的,平凡之中透著一股聰明勁,人際關系能力挺強的……
于是有了呂公和劉邦的初相識!到這會兒,嫁女的事兒是沒有的。就算劉邦是大富大貴,一見面就上趕著送閨女,這據情也太尷尬了,呂公也太卑微了,呂家也太掉價了,是不是?
呂公結識劉邦以后,鑒于第一印象不錯,後來還發生了嫁女事件,二人至少再度交往過幾次,外加道聽途說包打聽,呂公對劉邦有了較為全面的了解。
他知道了劉邦這人好酒好色,不務正業,缺點一大堆,但性格很好,人也寬厚,優點也是一大堆。
尤其是劉邦人際關系能力出眾!
在本縣官吏中,除了縣令、縣丞這些頂級大牛結交不上,劉邦有為數眾多的朋友,比如有「豪吏」之稱的蕭局長、曹局長,一般被人認為信息靈通、活動力很大的縣領導司機夏侯師傅,從事司法工作的任敖先生,等等。
在本縣富戶中,劉邦有地方豪門王陵、雍齒這樣的土豪朋友。
在本縣平民中,劉邦有同年同月同日生的盧綰這種鐵哥們,更有屠戶樊師傅、篾匠周師傅這等孔武有力、能打能殺的江湖粗人朋友。
反正朋友一大堆!而且這些人雖然目前還沒有後來那種文的武的能耐,但未來能有那種能耐說明他們資質和底子都不錯,換句話說,他們在沛縣的時候,都已經是或算得上人群中有實力的人物!
秦朝一個人丁興旺的縣也就幾萬戶,要是平均算的話,全國兩千多萬人口,一千多個縣,平均每縣才上萬人,就算豐邑原來也是一個縣,降格為邑并進了沛縣,沛縣相當于兩個縣的人口,那也還是幾萬戶的體量,算起來并不多。
而劉邦這樣一個擁有眾多有實力朋友的人,在幾萬戶的人群里已經屬于很有人脈了,更別說他本身就是管著八百戶人群的亭長。
好,簡要鋪墊完成,下面我們說嫁女。
嫁女這種家庭大事,肯定不會只因面相便出現的。劉邦能娶到呂公的女兒,說明他至少有一樣重要資質能被呂公瞧得上,或者是呂公需要的。
說到這,我們就要回顧下《史記》的原文了。
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
」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為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詘。酒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原季自愛。臣有息女,原為季箕帚妾。」酒罷,呂媼怒呂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之不與,何自妄許與劉季?」呂公曰:「此非兒女子所知也。」卒與劉季。呂公女乃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
在這段文字中,春秋筆法的正史所暗含的一個邏輯是:呂公與劉邦之所以有了關聯并嫁女,起因于呂家為躲避仇人而從單父縣(今山東單縣)遷居到沛縣。
為什麼偏偏遷到到沛縣?
因為單縣就在沛縣西北隔壁,緊挨著,離得近,沒事可以常回家看看,若有產業的話也不怎麼耽誤打理。更因為沛縣令——本縣最高行政長官,是呂公的好友,倆人不論是出于權力資本聯姻而結交的,還是出于老鄉之類的情感紐帶而結交的,反正呂公來了沛縣會有縣太爺罩著。
呂公能搬來沛縣,那仇人也能來沛縣。呂公都因為避仇而被迫搬家了,說明仇不是一般得大,大到有性命危險了。那麼如此大仇,可以推論仇人完全有動力尾隨跟到沛縣。
也就是說,即使呂公搬到沛縣,也完全有可能再度面臨仇人的追砍什麼的。
沛縣令是能罩著呂家,但他是縣令,年終有政績考核,過幾年還會有升遷或輪換的,不可能長期在沛縣待著。那麼,沛縣令要是走了,呂家該怎麼辦?
流水的縣令,鐵打的土著。這不需要結交土著嘛?
也不是誰都結交。呂公要結交那種能幫他對抗仇人迫害的土著。
正好通過縣府約飯,劉邦進入了呂公的視野,并且呂公在此之后知道了劉邦是他所需要的那種土著。或者說,劉邦亭長有他所需要的那種資源。
劉邦有什麼資源?
早年年少輕狂做過游俠,外出游歷過,見聞和見識是有的;身上有武藝,作為亭長也抓過盜賊辦過案子什麼的,打打殺殺是沒問題的;既有蕭局長等吏員朋友,能玩文的,也有樊師傅等江湖朋友,能玩武的。
也就是說,劉邦有能力幫他打發仇人(可以合乎邏輯地猜測,在呂劉相識到呂公嫁女這期間,劉邦就幫呂家打發過仇人,立過功,當然純猜測),再換句話說,劉邦有能力在沛縣令之外,為呂家構筑起第二道防火墻!
這樣一來,呂公結交原本八竿子打不著的劉邦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結交是看中人家的資源,想要人家的資源需要自己手里有資源,拿資源換資源才行!(相信體制內人士對此應心有戚戚吧)
呂公有什麼?從後來呂雉劉邦結婚后,倆人仍然過著「詩意」的耕織田園生活(其實就是種地)來看,呂家也許是商戶小地主,日子還不錯,但應該不是張耳、陳馀的姻家那種一經結婚便能讓女婿從此過上幸福生活的土豪富戶!
那麼呂公還有什麼資源?女兒!還有什麼手段能結交有實力的土著?聯姻!
這個史書沒提供直接依據,但是即便在筆者老家的鄉村里,外來戶通過聯姻與本村土著大姓攀上關系,從而借重姻親來站穩腳跟,至少不被人欺負,也是司空見慣的策略!
好吧,我承認我們家五十年前就是這麼做的。
所以,呂公能通過聯姻的方式來結交土著,這在平民百姓間一點不稀奇。
在這樣一種邏輯下,呂公需要結交有實力的土著,而此時走進他世界里的正好是他所需要的那種人,那麼呂劉聯姻豈不順理成章了?
總之,呂劉聯姻不像咱們尋常婚娶那麼簡單,但也沒那麼多的傳奇甚至江湖色彩。如果我們把這事搞得太傳奇,那豈不是跟意在突出平民劉邦并不平凡的史官殊途同歸了?我們在理性剔除史書的玄幻情節和靈異事件的同時,也應理性避開這些情節和事件背后的那種寫作邏輯,更應避免它隨風入夜般成為我們今日書寫歷史的邏輯。畢竟,不被情節支配易,不被邏輯支配難。
個人見解,友情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