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愛玲一生不喜與人逢迎,她曾說:我有的時候覺得我就是一座孤島。
張愛玲在《對照記》中寫下:繁弦急管轉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經遙遙在望......其余不足觀也已。
若說張生性涼薄,其實是張愛玲一生不喜歡「欠人」,無論家人、愛人或者是朋友,追求「清爽」。
張愛玲與母親、與姑姑,與弟弟,可謂「堅壁清野」,其實也是受多了傷害,才學會了克制感情。
對于親情,對于奇特的母女關系,可詳見《小團圓》一書。1975年張愛玲寫下了自己的故事《小團圓》,前半部分都是在寫母女關系。
若說張生性涼薄,胡蘭成自是懂得,但也是傷害她頗深。
胡蘭成曾說,她世事經得很少,但是這個時代的一切都自會來與她交涉,好像「花來衫里,影落池中」。還有胡蘭成的那句名句「張愛玲是民國世界的臨水照花人」。
但就這樣一個人把張愛玲推向了更涼薄之地。張愛玲曾感慨「生活在這個世上,沒有一種感情不是千瘡百孔」。可見胡蘭成帶給張愛玲的錐心之痛。
若說張生性涼薄,不如說她孤傲,張愛玲也因這性格,平白多出了很多難事。
賴雅去世后,張愛玲去柏克萊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了幾年,人際關系不好,而被辭退。當時她經濟已極為窘迫。直至1976年,皇冠社出版《張愛玲全集》,她的經濟才大為扭轉。
張愛玲在《天才夢》里說:我怕上理發店,怕見客,怕給裁縫試衣裳。在沒有人與人交接的場合,我充滿了生命的歡悅。
若說張生性涼薄,她也不是完全不諳世事,甚至于有著世俗的進取心。
張愛玲明白錢不是頂重要,但她也享受錢帶來的樂趣,認同這個時代本就不是羅曼蒂克,她明白地表示過她喜歡錢。
她習慣用錢代表理性,并以此清算感情。張愛玲對貨幣如何保值也有自己的看法,她老年清貧,但逝去時也有近三萬美元存款。
若論生性涼薄,真如紅樓黛玉。其實更見真性情罷了。
張愛玲曾外祖父李鴻章,祖父張佩綸,到了父親一輩,已經難看「煊赫舊家聲」。張愛玲的一生,愉快的童年,崎嶇的成長,顛簸的中年,凋零的老年。
悲愴紅樓,也是自悼。張愛玲一生熟讀《紅樓夢》,她常以此為慰藉,并寫下《紅樓夢魘》一書,張愛玲曾說:「偶遇拂逆,事無大小,只要詳一會《紅樓夢》就好了。」
「我將一個人終了此生」,便是張愛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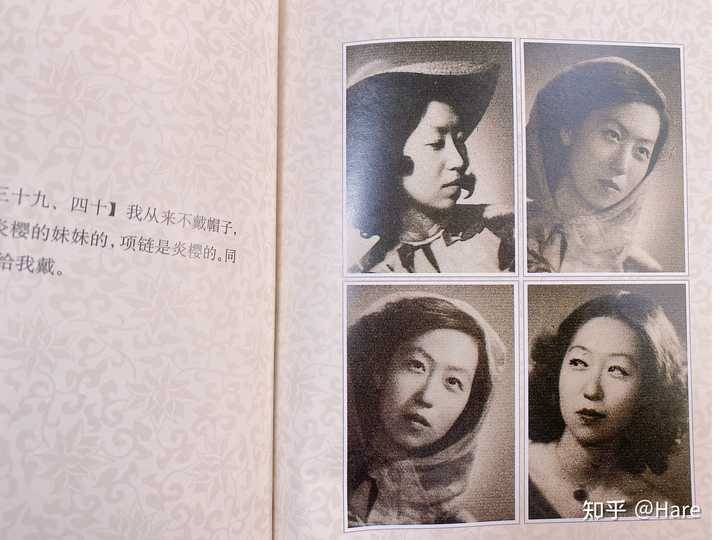
——
PS:我個人很喜歡并欣賞張愛玲,也不認為「生性涼薄」是什麼不好的詞匯,何況她不欺不欠不糾纏不清不趨炎附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