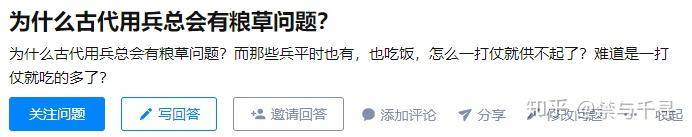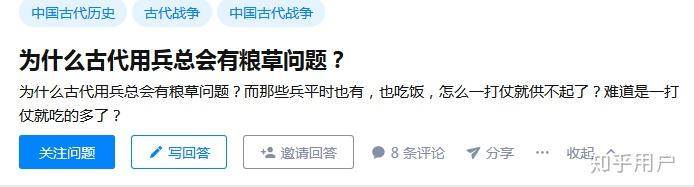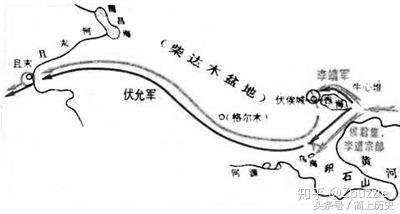因為古代打仗的時候最難的不是生產糧食,而是運輸糧食,尤其是要源源不斷的、按時按量的把軍需糧草運往前線,所需人力、畜力其實遠遠比真正上前線打仗的士兵要多的多。
宋代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中有一段內容對古代戰爭中運糧情況進行了大致描述,史學家葛劍雄先生翻譯過來大致情況是這樣:
每個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帶五天的干糧,一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一次可以維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能前進九天的路程。 兩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的話,一次可以維持二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個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個民夫背的米已經吃光,給他六天的口糧讓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每天吃四升米)。
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能前進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 三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一次可以維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個人,每天吃八斗米。減去一個民夫,給他四天口糧。以后的十七天三個人,每天吃六升。再減去一個民夫,給他九天口糧。最后的十八天兩個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計回程的話,只可以前進十六天的路程。(開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中間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
而三個民夫供應一個士兵,已經到了極限了。
如果要出動十萬軍隊,輜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夠上陣打仗的士兵只有七萬人,就要用三十萬民夫運糧。
再要擴大規模就很困難了(遣送運糧民夫返回要派士兵護送,因為運糧途中還會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這些減員的糧食供應護送士兵)。
「每人背六斗米的數量也是根據民夫的總數推算出來的,因為其中的隊長自己不能背,負責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們所減少的要攤在眾人頭上。
另外還會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們所背的也要由眾人分擔,實際上每人背的還不止六斗。所以軍隊中不容許有吃閑飯的,一個吃閑飯的人兩三個人供應他還不夠。
如果用牲畜運,駱駝可以馱三石,馬或騾可以馱一石五斗,驢子可以馱一石。與人工相比,雖然能馱得多,花費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時放牧或喂食,牲口就會瘦弱而死。
一頭牲口死了,只能連它馱的糧食也一同拋棄。所以與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可以說沈括的安排已經考慮到了很多必要的要素,但是這又是在沒有任何意外發生為首要前提下的。
所以在古代戰爭中的真實情況只能比這更為艱苦,糧食供應的困難往往在戰爭開始時就已經制約了參加作戰的人數和可以維持的時間。
即使到現代戰爭中,運輸能力較之1000多年前的宋朝有了突飛猛進的變化,運糧也依然是最重要也是最難的問題。
比如在朝鮮戰爭中,在一段時間的交戰以后,美軍逐漸發現了志愿軍的一個作戰特點,那就是由于補給不足,往往發動一次猛攻只能維持一個禮拜的時間。
每次戰斗只要超過一個禮拜,志愿軍基本就會不戰自退,美軍把這稱作「禮拜攻勢」。
而原因就是在于志愿軍的后勤補給每次只夠維持一個禮拜時間。
所以,明白為什麼古人一直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