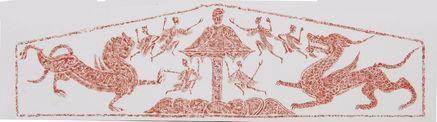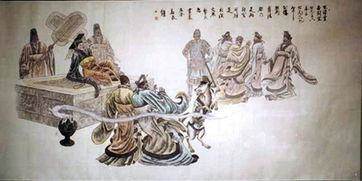在理解漢代外戚政治時,我們需要記住兩條基本原則:一、漢家與外戚共治天下;二、一朝天子一朝外戚。
第一條原則意味著,在漢代,外戚輔政有著天然的正當性,「外戚干政」本身就是漢家制度的一部分,這也是漢代與后世最根本的不同,「外戚不得干政」的祖訓對于漢代完全不適用。
第二條原則意味著,在漢代政治習慣中,外戚的起落與皇帝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旦皇帝去世,舊外戚也將被新外戚取代,從而喪失輔政的合法性,這在一定程度上也保證了外戚的流動性。
以下本回答將主要聚焦于西漢時代,總體而言,西漢時期不同于東漢,此時的外戚政治仍屬于可控范圍之內,諸如呂后稱制、王莽代漢等情形實際上疊加了更為復雜的因素,不能簡單視為外戚干政的結果。
在下文中,本回答將首先關注西漢時人對于外戚政治的觀念,從而論證此時外戚輔政的正當性,之后將個案聚焦于不同時期外戚政治的具體狀況,分析外戚政治對于西漢的影響程度。
最能夠說明西漢外戚政治正當性的,是王莽專政時期申屠剛的奏疏。此時王莽第二次出任大司馬,意欲摒棄平帝外戚獨攬朝政,因此不允許平帝外戚進京,申屠剛由是上書:
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隙,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今馮、衛無罪,久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
申屠剛在此直接將援引姻戚視為「漢家之制」,并據此要求平帝外戚共同進京輔政,鮮明的體現出了外戚政治在漢代的重要性。
為了更生動的說明這種影響,我們來聚焦于這樣一個詞語:肺腑。
在史記中,「肺腑」一詞一共出現了這樣幾次:
及孝惠訖孝景間五十載,追修高祖時遺功臣,及從代來,吳楚之勞,諸侯子若肺腑,外國歸義,封者九十有余。蚡以肺腑為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
肺腑一詞在今日語境中近似于「近臣」,然而如果考察史漢中的語義,我們會發現肺腑有著更為具體的含義。
在上述用例中,「諸侯子若肺腑」指代的同姓王,中間三例均指田蚡,最后一例指代衛青,諸如主父偃、嚴助等內臣則未見以肺腑自稱之例,考察漢書的用例則大體相同。
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認為,肺腑一詞在漢代有著比今日更為狹窄的含義:宗室與外戚。而這種反過來說的意思,就是外戚與宗室,并為肺腑。
與之類似的還有「骨肉」一詞。在霍光去世,宣帝親政以后,霍家權勢被許、史兩家取代,任宣便勸慰霍禹:「「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說明在漢代外戚輔政以及更替都屬于正常現象。
實際上,這樣的例子并非少數。在漢書外戚傳的開頭,班固便援引史記: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
根據徐沖考證,作為東漢重要史籍的東觀漢記在體例上同樣沿用了史漢《外戚傳》的設置,然而到了南朝范曄編纂《后漢書》時則將《外戚傳》改為《皇后傳》,這也從側面說明,在漢代,人們對于外戚政治的觀念與后世并不相同。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例子是元帝時蕭望之與弘恭、石顯等人的黨爭,在這場政治爭斗中,蕭望之直指二人的宦官身份:
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對于蕭望之而言,弘恭、石顯刑余之人的身份已然構成了一種原罪,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石顯、弘恭一方對于外戚的態度:
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望之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
在石顯、弘恭的攻訐中,疏退外戚、毀離親戚構成了蕭望之的重要罪狀,而面對這種指責,蕭望之盡管同樣對外戚作出了批評,但是卻不再像攻擊宦官時那樣強勢:
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
結合蕭望之最終的失勢來看,西漢時期外戚在政治上的確占據了重要的位置,盡管政爭的雙方均非外戚,卻仍然繞不開外戚這一重要話題,即使是蕭望之這樣的耿直儒臣,在面對外戚這一話題時也不似指責宦官時那樣強硬。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初步認為:在漢代,關于外戚政治的觀念與后世存在很大區別,外戚輔政有著天然的正當性,反而是試圖阻止外戚輔政的人會被視為有意專權。
那麼為什麼在漢代會形成此種觀念呢?就在申屠剛將「猶援姻戚」視為「漢家之制」時,另一條與「漢家之制」的材料為我們揭示了這種觀念的來源:
夏四月,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
漢代對于「孝」的推崇,間接影響了時人對于外戚的態度,二者相互融合,最終成為了外戚政治的正當性來源之一,任用外戚恰恰正是皇帝「孝」的體現。
一個與之密切相關的觀念,就是彼時的母族觀念。考察秦漢時期的律令,我們會發現彼時的父系觀念并不像后世那樣強烈,比如《置后律》關于爵位繼承的規定中便給女性保留了相應的位置:
毋子男以女,毋女以父,毋父以母。
此律意為,爵位繼承首先考慮兒子,如無兒子則由女兒繼承,沒有女兒由父親繼承,父親去世則以母親繼承。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唐律疏議》中關于繼承的原則:
無嫡子及有罪疾,立嫡孫;無嫡孫,以次立嫡子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子;無庶子,立嫡孫同母弟;無母弟,立庶孫。曾、玄以下準此。無后者,為戶絕。
《唐律疏議》中已經將繼承完全限定在男性序列之中,展現出漢唐之際的重要區別。
這樣的觀念展現在日常活動中,就是漢代存在子從母姓、重視異父同母關系、女性出嫁后所生之子仍然被視為母族之成員等諸多在后世看來難以理解或者認同的現象。
最為典型的便是田蚡之例,田蚡與王太后同母異父,但是在武帝即位之后,田蚡仍然被視為外戚的重要成員得任高位,基于王太后以及王太后之母兩位女性,武帝與田蚡得以基于甥舅關系被聯系在一起。
同樣是武帝,在聽聞自己在民間有一位同母異父的姐姐時,武帝表現出了極為積極的態度:
初,皇太后微時所為金王孫生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帝曰:「何為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
總而言之,在漢代,父系的支配地位并未完全形成,母族在社會生活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這構成了漢代外戚政治正當性的基礎。
在解釋過漢代外戚的正當性問題后,我們再來看一看西漢時代對于外戚的具體政策。
總體而言,西漢皇帝對于外戚主要采取了兩種統治策略:
第一種,給予外戚實權,但同時頻繁以新外戚取代舊外戚,防止任何一家做大,最為典型的便是武帝。
第二種,同時冊立多家外戚,但是并不會給予任何一家實權,使其占據高位而已,最為典型的便是宣帝,其次是哀帝。
武帝之事毋庸贅述,先是以田蚡代竇嬰,后以衛青、霍去病代田蚡,后又試圖以李廣利取代衛氏,體現出其對于朝堂強大的掌控能力。
宣帝事則可以稍微詳細說明,由于武帝去世后留下的權力真空,政治中心被霍光等內朝官員掌控,西漢中期迎來了一段少有的沒有外戚的時光(盡管嚴格來說霍光也是外戚)。然而伴隨著宣帝的親政,宣帝重新恢復了西漢的外戚傳統,并且一封便是妻家、母家、祖母家三家。
然而宣帝對于外戚的任用同樣有所考慮,最為典型的便是黃霸請封外戚史高為太尉一事,宣帝對其展開了嚴厲的批判:
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興文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帷幄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
宣帝一方面肯定了史高作為外戚、肺腑的親近地位,另一方面對于其權力堅決控制。這一原則在哀帝時代得到了延續: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丁、傅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勢,權勢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
縱觀西漢一代,在這兩種統治策略之下,外戚政治上并未造成真正的動蕩,西漢時代最為著名的外戚干政,其實是多種因素疊加之后的結果,不能單純視為外戚政治的結果。
最為典型的便是呂氏,呂后稱制并非單純的外戚干政,呂澤、呂釋之本身就是漢初功臣的一員,早在高帝在世時他們便得以因功封侯,呂后此后所封呂氏諸王大多也為二人子嗣。
另一個例子是成帝以降的王氏家族,盡管王氏家族的確達到了權傾朝野的地位,但是他們同樣遵循著「一朝天子一朝外戚」的慣例,在成帝去世、哀帝即位以后數月之間便被清出權力中心,如果不是哀帝的突然去世,王莽絕難有代漢的機會。
具體到王莽代漢這一問題而言,王氏外戚的權勢的確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這并不是充分條件,諸如內朝的崛起、儒學思潮的興盛都共同導向了這一結局,因此就此事而言,王莽個人的特殊性顯然要重于王氏本身。
最后做一個總結吧,正如我一直以來強調的觀點:秦漢時代是帝制形成的關鍵階段,這句話反過來的意思就是,在秦漢時期,帝制尚未真正形成,因此我們不能夠以后世時代的觀點審視秦漢。
外戚政治同樣如此,在彼時,人們并未將外戚視為洪水猛獸,他植根于當時的社會觀念之中,是漢家故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