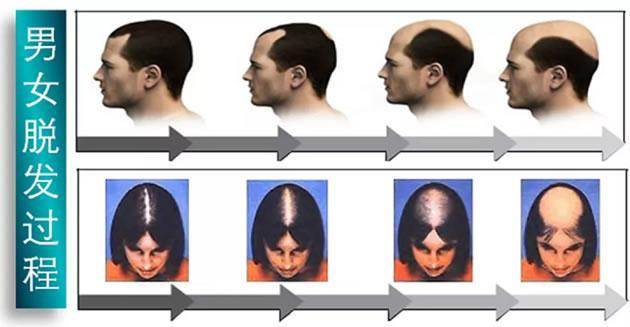我年近 40,但并沒有發福,身材還算結實。
那天,我遇到了那個,符合我內心深處的審美的女人。
我確定,在我的世界里,從未交往過這樣的女子。
于是,就算再自責,我也默許了她闖進我的世界。
我叫袁亮,遇到蔣桃時我 20 歲,在北大讀大三,正值青春年少,意氣風發。
當時我是院學生會主席,也算是學校的風云人物。
蔣桃是我人生中第一個追求的姑娘,是我一見鐘情的人,是我的初戀。
我追蔣桃花了整整三個月,不長也不短。
我是真心喜歡蔣桃,在她終于接受我之后,我全心全意地經營著我們的感情。
1998 年,我和蔣桃畢業了。
北大畢業生找工作并不難,我和蔣桃畢業后都留在了北京。
我被一家剛在中國開設代表處的外資投資銀行錄用了,蔣桃也在一家國企找到了一份有事業編制的工作。
我和蔣桃在南二環的老居民區里租了一個開間,從此開始了充滿油鹽醬醋的同居生活,時光開始復刻一般飛速流逝。
蔣桃在西單上班,我在建國門上班。
2001 年,周星馳的《少林足球》上映。
我買了碟片,照舊晚上和蔣桃擠在一起觀看。
看到激動處,我學著周星馳的樣子站在茶幾上,用粵語仰天長嘯:「人若無夢想,和咸魚有什麼兩樣!」
蔣桃被我逗得笑倒在沙發上。
我跳下茶幾,蹲在蔣桃面前認真地說:「講真的,桃子,我不想做咸魚,我想去美國。」
「美國?」蔣桃嚼了一半的浪味仙停在空中,隨即搖搖頭撲哧一聲,仿佛我說了一個很好笑的笑話。
但我是認真的。
在投資銀行駐華代表處工作,雖然實際業務有限,但同事都是從美國派來的華爾街精英,聽他們講美國資本市場,講亞洲的宏偉藍圖,我的眼界和心胸也跟著打開了,又豈能容許自己從此蝸居在這方舊土地上。
2002 年的冬天,我拿到了麻省理工學院的 MBA 錄取通知書。
我接到麻省理工學院招生辦電話的時候,我的手都在發抖。
當時我正在吃晚飯。
我放下電話對蔣桃說:「我被麻省理工學院錄取了。」
當時,蔣桃的筷子停在空中,整個人愣住了。
「蔣桃,嫁給我,跟我去美國。」
我激動地握住蔣桃的手,曾經醞釀千百遍的求婚,居然就這樣在情急之下脫口而出。
那天晚上,我和蔣桃喝了很多酒,桌上的空啤酒罐整整齊齊擺了一排。
那晚我絮絮叨叨說了很多車轱轆話。
「我付出那麼多,因為我想讓你過上好日子。」
「跟我去美國,我們從此過好日子。」
「蔣桃,我一定會讓你過上好日子。」
我一直自顧自地說,蔣桃只是一直夾菜,默默喝酒。
後來我喝多了,蔣桃也喝多了。
我抱她到沙發上,將她摁在身下,瘋狂地吻她,一遍一遍說:「嫁給我,蔣桃,你嫁給我。」
待我起身想要脫掉她的衣服,卻見她已滿臉淚水。
「寶貝,你怎麼了?」我捧著她的臉問。
「袁亮,你知道嗎?你的給予,對我而言也許是失去。」
蔣桃伸手抱住我,在我的耳畔呢喃道。
之后兩三日,蔣桃一直心事重重的樣子。
她烤焦了一條魚,拿鍋的時候又燙到了自己的腳。
「你真的不想去美國嗎?」我終于忍不住問。
我和蔣桃之間爆發了前所未有的一次爭吵。
我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她,我去了美國可以賺更多錢,可以擁有自己的房子,可以讓我們的孩子成為美國人……
蔣桃說她要那麼多錢干什麼,她就喜歡自己的小出租屋,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中國人。
最后蔣桃沖我聲嘶力竭地喊:「袁亮你為什麼這麼自私,為什麼要我為了你的夢想放棄我喜歡的生活?」
我怔住,竟被她嗆得說不出話來。
我一屁股坐在沙發上,空氣凝固。
「蔣桃,我們是要在一起的,不是嗎?」我憋了半晌,帶著哭腔說。
當晚大吵之后,蔣桃搬去了她的朋友家。
過了很久,我聽見了門鈴響。
我怔著站起來,看著門打開,蔣桃出現在那里,瘦瘦小小的身影背著一個舊書包,孤零零地站在漆黑的走廊里。
「袁亮,我想好了,我愿意和你去美國。你說結婚的事情還算數嗎?」蔣桃仰頭看著我,嘴里微微喘著氣。
「算數!當然算數!」我拖鞋都沒顧上穿,光腳幾步沖到蔣桃面前,緊緊擁她入懷。
我和蔣桃的婚禮是在北京一家湖南菜館舉行的,請了五桌客人,除了遠道而來的父母和個別親戚,幾乎都是大學同學。
我倆的禮服都是從五棵松的地下商店買的,蔣桃穿了一條白色的魚尾裙,簡單而顯身材。
我在敬酒的時候還會回頭瞄一眼身邊的蔣桃,前凸后翹,唇紅齒白。
在其他女同學的簇擁下,我仍然覺得她是最美的那一個。
讓我再選一次,我追的人還是她。
而如今她已是我的女人,經官方認證了的,我的女人。
蔣桃成了我名正言順的妻子。
她告別了家人、朋友,辦了停薪留職,隨我登上了飛往波士頓的飛機。
美國,我來了。
我在心中默念。
2003 年秋,我帶著蔣桃來了美國。
讀 MBA 的兩年,我的心里一直是有負擔的,我背負著幾十萬元人民幣的借款,背負著蔣桃為我做的犧牲,背負著像鞭子一樣的夢想。
在壓力特別大的時候,人更容易成功。
讀 MBA 的第二年,我沒日沒夜地投簡歷,面試,最終在距離畢業還有幾個月的時候拿到了一家頂尖投資銀行紐約總部的聘書,做衍生品交易員,年薪 10 萬美元,獎金另計。
10 萬美元,這是我父母用了一輩子也沒有攢出來的一筆錢,從這一刻起,他們的終點,不過是我的起點。
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蔣桃,我們的人生才剛剛開始。
2005 年,我畢業后帶著蔣桃遷往紐約。
這次遷徙蔣桃不再像上一次反應那麼大,很順理成章地跟著我來了。
她終于開始接受長期居住美國的事實,開始表示喜歡上了美國清簡的環境,開始正經計劃自己以后的生活。
而她的計劃很簡單,就是生一個孩子。
這不是一個難以實現的計劃。
2006 年,蔣桃在紐約上西區的醫院里生下了一個男孩。
我給他取名叫查爾斯,因為當時正值夏天,我憶起查爾斯河畔,綠樹成蔭。
距離查爾斯兩歲生日還有一個月的時候,蔣桃告訴我,她又懷孕了。
我知道她喜歡孩子,她也能夠把我們的孩子照顧得很好。
我將她擁入懷中說,老婆,辛苦你。
2009 年春天,蔣桃又生下第二個男孩,跟著老大查爾斯的名字,老二亦以河流命名,叫哈得孫。
蔣桃躺在床上,微笑著,望著我抱著小哈得孫站在窗前,給他看窗外瞬息萬變的世界。
這的確是個瞬息萬變的世界。
2009 年,我收獲了第二個孩子,卻丟掉了工作。
金融危機來了。
後來我常跟新入職的年輕人說,除非親歷,否則你無法體會金融危機期間那種恐慌與絕望。
2008 年 3 月 10 日對于紐約華爾街上的職員們來說,只是又一個平淡無奇的早晨。
當紐約證券交易所開市的鐘聲響起的時候,誰也沒有想到,擁有 85 年歷史、3504 億美元資產、180 億美元現金,并被視為華爾街象征之一的貝爾斯登公司,竟然瞬間不復存在。
而從這一家公司的倒閉開始,華爾街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我所在的投資銀行也很快陷入了危機。
那段時間,我的心情無比焦灼。
我有養家糊口的壓力,而如果在那種情況下被裁掉,是肯定找不到下家的。
美國的局勢越來越糟,被裁員似乎是早晚的事。
蔣桃一邊給懷里的小哈得孫喂奶,一邊抬頭對我說:「老公,不然我們回國吧。」
我抬頭瞪了她一眼,心中憤然。
我并不是排斥回國,而是我無法接受將回國作為一個消極的退路。
假如我開始往后退,心中仿佛總有一個恐懼的疑問,若有一日,退無可退該如何?
「你們不都把中國叫大中華區嗎?大中華,怎麼不容你一個家。」
蔣桃像是在跟我說,又像是在向懷中的孩子念叨。
大中華,是啊,中國除了內地,還有香港啊。
我豁然開朗。
數月后的一天,拖著七七八八的行李,我們就像逃荒一樣站在了香港機場熙攘的人群中。
我的未來,從此將和這座嶄新的城市關聯起來。
此情此景,像極了我當年帶著蔣桃第一次落地美國的畫面。
不同之處在于,我的懷中多了一對孩子,我的兜里裝著 100 萬美元。
我再次踏實地坐在了明亮的辦公桌前,成了一名投資銀行另類資產投資副總監。
我把我們一家四口的照片擺在辦公桌上,盯黑色的指數屏幕盯得久了,轉頭就能看到蔣桃和孩子們燦爛的笑容。
這也許是我心中最柔軟的一部分,是我認為我為之奮斗的一切。
卻不曾想,在看似波瀾不驚的中環,卻迎來了我人生中最波濤洶涌的十年。
2010 年,初到香港,我和蔣桃住在堅尼地城的酒店公寓里,公司每月報銷 4 萬港元房租。
但兩室一廳的公寓不足 700 平方英尺(約 65 平方公尺),一家四口難免局促。
于是我們就開始滿香港看房。
後來我們在港島南邊看中了李澤楷開發的一個高端樓盤,依山傍海,院子里有四個游泳池,會所里陳列的都是精致的藝術品,出門便是草地海灘,有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的白人,還有奔跑著的千奇百怪的狗。
當時,三歲的查爾斯帶著剛學會走路的哈得孫在無邊泳池畔的噴泉里奔跑,哈得孫一屁股坐在了一個噴泉泉眼上,水花從他屁股四周噴濺出來,哈得孫一邊拍水花一邊發出嘎嘎的笑聲。
那一刻我便決定要在這里置業。
我付了五成首付,買了一套 1600 平方英尺(約 150 平方公尺)的四居室。
當時把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但十年后回頭看,當時真是做了正確的決定。
這個樓盤十年后成了港島最宜居的小區之一,房價翻了四倍,這都是后話。
蔣桃帶著兩個孩子,順理成章地留在了家里。
香港在某些角度和日本很像,男人在職場上腥風血雨,女人在家里相夫教子。
在我們住的小區里,女人大多是不工作的,到了白天,院子里都是女人、孩子和菲傭。
只有晚上和周末能夠看到行色匆匆的男主人歸來。
雖然我們的經濟條件已算寬裕,但蔣桃還是喜歡坐公交車去香港仔的當地人開的菜市場買菜。
我辦公都用英文,始終沒有學會廣東話。
但蔣桃來了一年,就在菜市場阿公阿婆的實戰操練下,不僅學會了廣東話,還會了不少俚語。
兩個孩子上學后,蔣桃又搖身一變,從學校申請專家變成了課外班專家。
香港的學校在孩子 7 歲以前都是上半天課。
蔣桃就早上帶查爾斯去上各種課外班,下午帶哈得孫去上各種課外班,如此往復,一周無停歇。
查爾斯和哈得孫都令人欣慰地茁壯成長著。
兩個小家伙都能講流利的中英文,不像院子里很多菲傭帶大的孩子大多能講一口菲律賓英語,卻丟了老祖宗的普通話。
查爾斯 6 歲就成為香港中西區圍棋比賽的小齡段亞軍。
哈得孫 4 歲就學會了游泳,還可以和哥哥一起下圍棋。
一切都那麼順利美好,妻賢子孝,我仿佛過上了小時候看的 TVB(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港劇里陽光明媚的富家生活。
2012 年,一家外資私募基金向我伸出橄欖枝,讓我做中國區投資副總監。
我幾乎沒有猶豫就決定接受這份工作。
畢竟除了收入的上升,從賣方變成買方本身也是每個投資銀行人的理想。
唯一的問題是,這份工作將意味著要頻繁出差。
這家私募基金的辦事處在香港,但投資的項目都在內地,因此我幾乎每周都要飛北京上海。
我對蔣桃說,這份工作會經常出差。
我以為蔣桃會勸我再考慮,會告訴我孩子需要父親陪伴。
但如今的蔣桃早已不是十年前那個嚼著薯片不肯去美國的姑娘了。
她是一個務實的妻子和母親。
「沒事,不就是出差嗎,家里我一個人沒問題。」蔣桃淡然道。
于是我們家也成了香港「候鳥家庭」的一員。
周一到周五,我幾乎都在內地出差,每周五的晚上坐晚班飛機回到香港。
蔣桃平時就在菲傭的幫助下帶兩個孩子。
我的馬可波羅卡很快就升級到了鉆石,每當我出現在國泰航空的飛機上,空姐都會特意走過來說:「袁先生,歡迎您再次乘坐我們的航班。」
當我和空姐及酒店前台人員越發打成一片時,在我的家里,我逐漸成了一個「附加品」。
沒有我成了這個家庭的固有模式,蔣桃和菲傭按照兩個孩子的日程日復一日地正常運轉,上課、聚會、外出,執行著各種與我無關的生活計劃。
每當我周五晚上回到家里,往往都已是深夜。
蔣桃最初還會等我回家,後來習慣了,也不再等我,只是在客廳給我留一盞燈,然后我抹黑走進臥室,換衣服,默默躺在早已熟睡的她身邊。
周末是我唯一和孩子們相處的時光。
查爾斯和哈得孫周六日都有游泳課,我就一個人在家里睡個懶覺,煮一杯咖啡,看一會兒電視。
在其余所剩無幾的時間里,我會帶著孩子們下樓踢球,或者和蔣桃一起帶孩子們登山、看電影。
我努力讓我和孩子們在一起的時光變得有品質。
我想我能做到。
我和他們一起大呼小叫,一起玩大富翁,也舉著台燈和地球儀站在沙發上給他們講公轉自轉、宇宙黑洞。
我能勉強維持成為一個好父親,卻難以維持成為一個好丈夫。
除了夜里睡前的片刻時光,我幾乎沒有任何和蔣桃獨處的時間。
即使是周六晚上,我和蔣桃唯一可以獨處的夜晚,我也常常自己看球看到困倦,蔣桃忙完兩個孩子,也是一身疲憊地上床,兩個人聊聊孩子的事情,便各自睡去。
偶爾我發覺很久沒有和蔣桃親密,于是試著摸黑去撫摸她。
有時她會將我推開,說太累了。
有時她不拒絕,但我也早已不再是大學時代的那個我,往往也是五分鐘簡單了事。
我想,所有人到中年的夫妻,都是這樣的狀態吧。
從愛情變成親情,從愛人變成家人,從感恩變成理所應當。
周一到周五的我,逐漸習慣了內地的生活。
我突然覺得,之前的十年都蹉跎了。
什麼美國,什麼香港,不過是靜如止水的成熟市場。
而北京、上海、深圳,則正處在萬馬奔騰的黃金時代。
天天奔走在各個項目企業之間,聽創業企業家們滿懷激情地勾畫藍圖,聽投資者們激情滿滿地傳遞著新的想法和故事。
每個早晨,人們都被夢想喚醒,每一封郵件、每一個聚會,都傳遞著新的信息。
動輒上億的資本,就像洶涌的河水,奔去各個產業脈絡。
白天有喝不完的咖啡和龍井,晚上有喝不完的紅酒和茅台。
每天都在認識新的人,每個人都帶著新的項目和故事。
每天面對的是雪茄吧的金絲眼鏡,飯店包廂里泛紅的胸口,昆明飯店的綢緞長裙。
但無論怎樣紙醉金迷,每個人的心中都是清明的。
酒,要喝出怎樣的交情,要搞定多大的融資,沒人閑著無聊和你喝圖樂呵。
所以無論怎樣稱兄道弟,身邊的姑娘怎樣醉倒在肩頭,我都明白,大家終究只是業務關系。
直到遇到黃芙。
黃芙小我 7 歲。
我後來總拿她名字打趣,說她有黃蓉的烈,又有郭芙的倔。
我第一次見到黃芙是 2013 年夏天,在一個 TMT(科技、媒體、通信)產業論壇上。
當天來了包括 BAT(百度、阿里、騰訊)在內的很多領軍企業的人,吸引了很多投資者去參加,我也是其中之一。
但黃芙并不是來自領軍企業,也不是投資者,而是站在出場走廊邊上的突兀存在。
「您好,我是桃花島視頻的創始人黃芙。我們現在已經融到了天使輪資金,很多投資者都有興趣投我們的 A 輪,我也希望多聊幾家,這是我們的融資項目建議書,您看方便的話可以約個時間細聊一下我們的商業模式。」
我中場休息出來上廁所,突然冒出來一個身影,遞給我一本厚厚的印刷品,連珠炮似的說了一大串。
我的目光從印刷品上移至這個人影,聚了聚焦,原來是個姑娘。
我記得當天她穿著紅色套裙,一頭莫文蔚式的波浪長髮,面孔素凈,有一雙深深的像印度人一樣的眼眸。
黃芙就是這麼猝不及防、近乎唐突地闖入我的世界的。
我翻閱了她遞給我的宣傳冊,是一個強調原創精品內容的短視頻公司,名字別致,叫桃花島。
「黃芙,桃花島。」
我笑笑說,「有意思。」
黃芙一下笑了起來,印度人式的深眸頓時變成了彎彎的月牙。
真是個鮮活的姑娘。
我在心中說。
「好啊,我們可以約個時間聊聊。不過我們通常投的都是 B 輪和 C 輪,如果你不介意,我倒也不介意分享一些同類公司的經驗給你。」
我不由自主就應承了下來。
「太好了!太感謝你,袁總。」
黃芙看著我的胸牌說。
一周后,我和黃芙約在北京國貿的一家咖啡廳見面。
黃芙穿著一條亮黃色的連衣裙,系了一條細細的金色腰帶。
莫文蔚式的大波浪頭髮被束成了一個丸子,露出了她精致的臉型,尖尖的鼻子,微翹的下巴。
她給我大致介紹了一下她的項目和團隊:她是從英國畢業回國的,在 4A 廣告公司做了幾年,後來遇到兩個志同道合的合伙人,辭職后從前年開始創業。
「現在國家正在進行整體光纖改造,今后網絡速度會越來越快。網速的革命會催生怎樣的產業?我認為是視頻。」
黃芙認真的時候是不茍言笑的。
她用手指輕輕劃過桌上的冊子,一字一頓地說:「我認為視頻產業即將迎來黃金的十年。」
這些充滿前瞻性的言論從一個年輕姑娘嘴里說出來,變得格外有趣味。
我也跟著打開了話匣子。
「網速的革命的確會催生一批行業發展,包括視頻。但你有沒有想過,在這個廣義的領域下,到底是做內容提供者,還是做平台?生產內容,不如整合內容,成為渠道的掌握者。」
「你說得太對了,但我認為只有先掌握內容生產能力,才能進一步整合外部內容。
正所謂,攘外必先安內。」
黃芙講話尖銳,總能給我意想不到的對答。
那一次見面,我和黃芙聊了長達三個小時。
從網絡技術革命聊到視頻產業,從平台化趨勢聊到全產業去中心。
我和這個 80 后的姑娘,竟有了相見恨晚之感。
有個詞叫作「化學反應」,可以形容兩個人之間的氣場和火花。
我和黃芙聊完,突然對這個詞有了新的理解。
那次見面后,黃芙在我心中變得立體起來。
有時我會忍不住翻看她的臉書主頁,有穿著魚尾晚禮服的紅毯照,也有和團隊熬夜做產品的加班照,有她在加州參加行業峰會的工作照,有她和隊友一起劃龍舟的合影。
有時我會覺得,這個小我 7 歲的姑娘的生活,是我內心一直向往的狀態。
努力、自由、果敢、斑斕,她活出了我想要的樣子。
後來我介紹了幾位投資人給她。
其實我和這些投資人也不熟悉,但我就鬼使神差地為這個只喝過一次咖啡的姑娘賣了好幾次人情。
黃芙是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我介紹給她投資人,她自然要答謝。
距離上次見面一個多月后,她約我周日晚上一起吃飯。
我原本計劃周一再從香港飛北京,但看到她的信息,我立刻打電話給秘書,將飛機改成了周日中午。
蔣桃一邊幫我疊衣服一邊說:「孩子們周六都有課外班,原本想要周日全家去長洲島走走,這下又只剩我們娘仨了。」
我心生歉意:「今晚臨時有很重要的客戶要見。」
說完自己在內心咯噔一下,為什麼明明是「朋友」,脫口而出的卻是「客戶」。
後來想想,這一個詞的區別,其實早已明示著我心中有鬼。
夏天飛北京的飛機很容易晚點。
我原本買了下午 2 點的機票,結果卻一直晚點。
我一直在候機室和黃芙發信息。
「我到機場了。」
「有一點晚點,但愿能按時到。」
「又晚點了兩個小時,咱們晚些開始吃吧。」
「登機了,但到北京就 9 點多了,太抱歉,今天恐怕要爽約了。」
黃芙一直在發笑臉給我,安慰我說沒關系。
直到知道我的飛機晚點了 3 個小時,她依然表示:「沒關系的袁總,您什麼時候到了咱們再吃,大不了晚飯改夜宵。」
下了飛機,我拖著小箱子一路小跑,排隊出關的時候我一直在用鞋尖敲擊著地面,前面的人耽誤半分鐘彎腰取東西都能讓我怒從中生,不知是因為跑步還是因為怒氣,我能感覺到自己心跳加快。
跳下出租車,幾近絕望地走進餐廳,大部分客人已經離去,只剩下寥寥兩三桌。
在角落的位置,有個熟悉的身影站起來,沖我招手。
我心中頓時一熱。
當晚的黃芙穿了一條深藍色的斜肩連衣裙,頭髮散在肩上,她看見我,立刻綻開笑容,笑得鼻尖兩側皺起小皺紋,很像《月光寶盒》里剛見到至尊寶的紫霞仙子。
「抱歉,讓你等了這麼久。」
我深表愧疚。
「您幫我那麼多忙,我多等一會兒算什麼。
因為我明天又要出差,這次約不上,下次就不知要等多久了。」
黃芙笑道。
然而當我喊服務員點菜的時候,卻被告知,餐廳已經停止接單了。
「我帶你去一個我喜歡的酒吧,里面也有食物,做得還不錯。」
黃芙見餐廳要關門了,起身說。
黃芙帶我去了停車場,帶我上了一輛路虎。
「小姑娘開這麼大的車。」我說。
「這樣路上就沒人敢欺負我了呀!」黃芙俏皮地說。
黃芙驅車帶我去了三里屯一家酒吧,高高的酒台上擺著五光十色的瓶子,白人調酒師將杯子甩在空中表演著絕技。
我們點了兩杯金湯力酒,吃炸雞塊、薯條。
「抱歉,這個點兒只能請你吃垃圾食品了。」黃芙笑道。
這樣的氛圍自然是不聊工作的。
我們一邊飲酒,一邊分享著彼此的生活。
我給她看查爾斯和哈得孫的照片,黃芙驚呼:「好漂亮的孩子!」
她說孩子一定有個漂亮的母親,我說「沒有啦」,便岔開了話題。
「終日忙于工作,有時候覺得自己像個工作機器,能像今天這樣坐下和姑娘喝杯酒,實屬不易。」
我打趣道,但隨即又覺得仿佛有些冒犯。
黃芙倒并不介意,舉杯和我碰了一下:「我也是,自從創業以來一直全情投入工作,建設團隊,找投資,忙到最后老公也跑了。」
「跑了?」我驚詫。
「身為女性,我自求不受困于三尺灶台,亦可仰望遠方,與摯愛之人并肩前行。但無奈對方并不認同,反而越來越沒了共同語言。
」
黃芙淡淡地說。
如此樂觀熱情的女子,竟然有過一段失敗的婚姻,望著低頭飲酒的黃芙,一縷頭髮垂在眉間,我不禁突然產生一股前所未有的保護欲。
酒過兩巡,時間已近午夜。
「你住哪里?我叫代駕送你。」
黃芙說。
那個時間街上不好打車,我又何嘗不愿意和黃芙多走一程,便沒有推辭,隨她上了她的路虎。
代駕坐在前排,我和黃芙坐在后排。
「師傅,車上有女士,您開慢點。」
我交代代駕。
「好嘞,您不操心,您忙您的。」
代駕回頭沖我擠擠眼睛,一句不妥當的玩笑,加上車里昏暗的光線,讓氣氛突然變得曖昧起來。
汽車發動起來。
黃芙喝得有點暈,靠在椅背上,用手撐住頭,閉上眼睛。
「你還好嗎?」我情不自禁扶住她的肩,低頭關切地問。
她沒有躲閃,也沒有改變姿勢,只是點點頭,嗯了一聲。
我意識到我已經摟著她瘦削的肩,她的頭髮垂在我的手上,隨著汽車的顛簸輕輕掃動著我的皮膚。
我突然不知道從哪里來的勇氣,說出了一句震驚天地的話。
「我可以吻你嗎?」
使用 App 查看完整內容
目前,該付費內容的完整版僅支持在 App 中查看
??App 內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