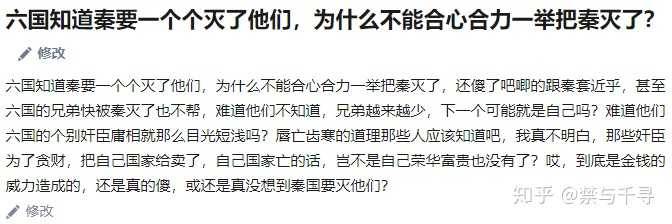之前其實寫過類似的問題[1],這回重新讀材料,想做一些無聊的考證,同樣也是為了拋磚引玉,和各位一起探討一個問題:六國究竟是什麼時候知道秦國想要統一天下的?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認識到兩個前提:
第一,「秦國想要統一」,是一個十分主觀的問題,和「在客觀上,秦國何時具備統一六國的實力」是截然不同的,而為了回答這個主觀問題,我們同樣需要依據具有主觀性質的材料:話語。
換句話說,「六國什麼時候知道秦國想要統一天下」,最直接的依據就是,六國之人何時提及了「秦國兼并天下的危險」,這種話語是比客觀形勢更為直接的依據。
第二,六國之人與我們不同,甚至與后世的割據政權也不同,因為他們從未經歷過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即使是西周時代的「大一統」,也只是一種以周天子為中心構建起來的多國政治秩序,而不是秦始皇式的物理統一。
這就意味著,對于六國之人,甚至同時代大部分秦國人而言,他們仍然處于一種「思想的囚籠」之中,就「秦國的統一」這一命題而言,對于時人來說最大的困難恰恰在于:大部分人或許根本想不到秦國竟然想要統一。
也正是因此,在秦真正完成統一后,王綰、淳于越才會提出繼續采取分封策略,東郡黔首才會在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楚地三老豪杰才會對陳涉說:「復立楚國之社稷,功宜為王。」因為對于戰國之人而言,統一仍然是一種「難以想象的常態」。
舉一個不恰當的例子,如果今天有人說美國想要爭奪世界霸權,我想大家都不會感到驚奇,但是如果有人告訴你美國想要統一全球,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覺得他有點大病。
在看過了「合久必分,合久必分」的中國歷史周期律之后,我們自然知道統一是歷史的大勢所趨,但是對于戰國之人而言,統一這件事并沒有那麼順理成章,甚至是難以想象的,也正是因此,我們才有必要去追問:六國,究竟是何時知道秦國想要統一的?
畢竟,我們正站在思想的牢籠之外,看著牢籠里的人。
(道理講完了,以下就是無聊的考證分割線了)
首先看一篇最著名的材料:《蘇秦列傳》。
《蘇秦列傳》里開篇便提及了:「以秦士民之眾,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可以說是典型的統一之心昭然若揭了。
此外,《蘇秦列傳》中對于六國的游說又存在大量「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的表達。
然而,歷來對于《蘇秦列傳》的真實性便存在非議,甚至司馬遷本人也認為「世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
尤其是上世紀《戰國縱橫家書》出土以后,更是進一步說明了蘇秦實為五國攻齊時代的人,其最重要的身份是燕國間諜,《蘇秦列傳》并非蘇秦之事。
一個最直接的矛盾是,蘇秦所描述的「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并非其所稱的惠文王初年的疆域[2],其文本內部也存在明顯矛盾。
當然,楊寬先生便認為,盡管《蘇秦列傳》并非如其所說作于惠文王初年,但是并非偽作,而應當改訂在昭襄王時期,被司馬遷錯誤的描述為蘇代事跡。
但是我認為這一觀點也很難成立,因為史記中關于蘇代入秦的描述是「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為齊使于秦。」
換句話說,昭襄王時蘇代是以「齊使」的身份面見秦王,這和作為民間策士力勸秦王實現統一的背景完全不同,《蘇秦列傳》中的內容無法安在蘇代身上。
在我看來,《蘇秦列傳》應形成于戰國末年以后,前面所提的「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和李斯列傳中所稱的「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完全一致。
此外,在《蘇秦列傳》身上,我們還可以從中挖掘兩個明顯不屬于戰國中期,而屬于戰國末期的表達方式:六國、郡縣。
首先說六國,受到《過秦論》《六國論》等名篇的影響,我們很容易把戰國中期以后的歷史視為「虎狼之秦VS山東六國」的歷史。
但是一個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實是:直到公元前255年,魯國被滅后,山東才真正只剩下六個國家。
「虎狼之秦VS山東六國」的敘事實際在長平之戰后的新形勢下,逐漸深入人心的歷史記憶,并一直延續到秦末之際。我們對于戰國的經典敘事實際上是在戰國末年才真正形成的新記憶。
換句話說,倘若在文本中頻繁出現「六國」,那我們便基本可以認定,該篇文字出于長平之戰以后的戰國末年。
另一個經典表達是「郡縣」。很多人都知道,郡在早期是一種「邊疆軍事區」而不是「縣的上級行政區」,郡是逐漸從軍事區演變為上級行政區的。
而游逸飛老師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認為,郡演變為行政區的過程十分晚近,可能是在秦王政親政以后才真正實現,而「郡縣」連用的表達,實際上正是郡-縣二級行政體制完成的標志。
在昭襄王中晚期的簡牘中,我們看到對于郡、縣的表述依然是「縣、十二郡」,而不是「郡縣」連用。反過來說,如果出現「郡縣」連用的表達,我們同樣推斷該篇文字應該出于戰國晚期。
如果考諸史記,我認為此種觀點是可以成立的,史記中「郡縣」連用的說法主要見于李斯以后,如「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又如韓非子存韓篇提及:「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
主要的兩個例外,一個是蘇秦列傳[3],一個是樂毅列傳[4],而這兩篇恰恰是真實性嚴重存疑的篇目。
基于以上分析,我認為基本可以斷定《蘇秦列傳》為戰國末年以后的作品,不能代表戰國中期的情況。
第二篇需要辨析的篇目是《楚世家》,在楚懷王三十年時,昭襄王曾誆騙懷王入境,此時昭雎阻攔懷王稱:
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
然而此處存在的問題是,《楚世家》的記載與《屈原列傳》的記載存在不同: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
兩段記載前后背景完全一致,但是勸阻者有所變化,并且少了十分重要的「有并諸侯之心」一句,此處可能存在后世的發揮、修改的情形。
第三篇要注意的篇目是《韓策三》第四章,或謂韓王曰:
秦之欲并天下而王之也,不與古同。事之雖如子之事父,將猶亡之也。
這一篇是我目前看到最早的提及秦國存在吞并天下可能的文字,楊寬先生依據「秦王欲出事于梁,而欲攻絳、安邑」將其斷在昭襄王二十年。
我個人對本篇有所懷疑,畢竟在昭襄王二十年時,秦國甚至還沒打下郢都,在此時判斷秦國將要吞并天下,似乎有些太早,但是我對于本篇并沒有像蘇秦列傳那樣充足的論據,只能由于本篇缺失作者、篇目內容短小保留一定意見,求教于各位方家。
據此,《韓策三》第四章是我個人目前所見最早揭示出秦國可能統一天下的話語表達,時為昭襄王二十年。
第四篇文獻是長平之戰前魏無忌警告魏王的記錄:
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目前來看,我個人認為這篇文獻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但是魏無忌的觀點反而值得注意。
信陵君一方面認識到了秦有「盡亡天下」之心,一方面卻又保留了「入朝而為臣」的可能。
占據后見之明的視角上,我們早已知道,在秦王政和李斯構想的永恒帝國里,根本沒有給六國留下「入朝為臣」的空間,這也進一步體現出,即使是那些的「先知」,對于未來的發展也沒有完全預料到。
對于上述材料的分析,我們要注意兩個問題:
第一,戰國策的單篇文本同樣可能是層累形成的,不同章節可能形成于不同時間,比如我們判斷魏無忌言論在長平之戰前的依據是「夫越山逾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閼與之事,秦必不為也。
」
但是如果本篇是層累而來,那麼就存在一種可能:前面對于秦國形勢的分析寫于長平之戰前,而對于未來不利形勢的警告可能來自于長平之戰后。層累現象的存在無疑會加大給戰國策斷代的難度。
第二,更為重要的問題是:這些文字都來自六國之人,在勸諫國君時,往往會對后果有所夸大,是否能夠完整反映時人的觀念,其實是需要打折扣的。
一個明顯的證據是:在當時的秦國,甚至都沒有這些先見者看的更遠。我目前并未看到,在惠文王、昭襄王時期,有以「兼并天下」向秦王獻策的記錄,甚至范雎入秦時給昭襄王畫的餅是: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
此時是昭襄王四十一年,如果早在昭襄王二十年時,秦國便有統一天下的考慮,那麼范雎此時給照相畫一個「霸事可成」的餅,似乎有些太過不識時務了。
昭襄王接受了范雎所畫的餅,一定程度上也反過來說明,對于此時的秦國而言,統一遠遠不是一個足以展望的現實目標。
與之類似,在長平之戰后,《韓非子·初見秦》的作者[5]畫的餅是:
臣昧死愿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荊、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鄰諸侯之道。
從昭襄王晚年的一系列動作來看,與其說秦有意兼并天下,不如說他更多是在嘗試成為新的「周天子」,而這也與范雎、初見秦的觀點一致:
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賓。……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年,王郊見上帝于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韓王衰绖入吊祠,諸侯皆使其將相來吊祠,視喪事。
秦的統一真正成為一種迫在眉睫的共識,仍要等到秦王政親政以后,李斯、尉繚曾分別如此勸諫:
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原大王毋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
與之類似,韓非在存韓時也勸諫秦王政:
且夫韓入貢職,與郡縣無異也。均如貴臣之計,則秦必為天下質矣。陛下雖以金石相弊,則兼天下之日未也。
這一年,是秦王政十四年,三年以后,韓國滅亡,秦統一六國的號角正式吹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