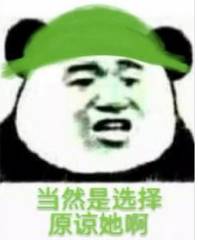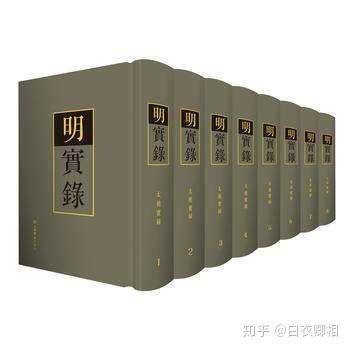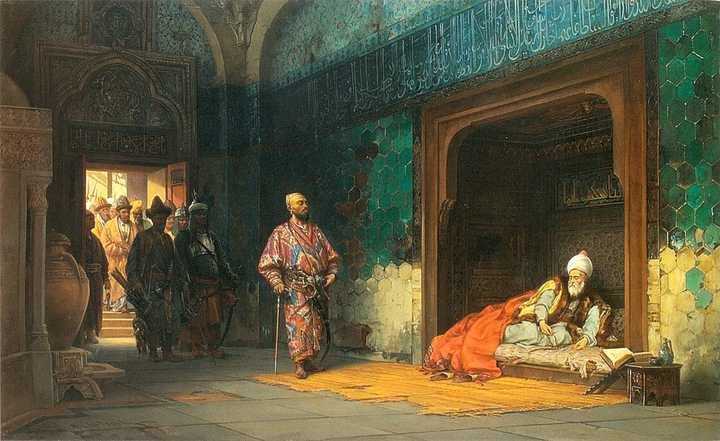各種歷史資料對朱棣形象的兩種截然不同的塑造,可以用新歷史主義觀來解釋。
例如說到司馬相如,大家或許都會想到他和卓文君的愛情佳話以及他作為漢賦大家的文學史地位。然而《史記》、《漢書》、《西京雜記》里記載的司馬相如卻是一個靠卓文君謀財上位的心機婊鳳凰男。諸君請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對司馬相如的記載: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
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于是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繆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后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愿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著犢鼻裈,與保庸雜作,滌器于市中。卓王孫聞而恥之,為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
以上「繆」字為假裝之義。
首先司馬相如買官來做,這種行為便見其氣節不高,后又與臨邛縣令王吉串通套路卓文君,更見其心機頗深。司馬相如套路卓文君顯然是求財不求色。《史記》對司馬相如的外貌倒有所記載,「相如雍容閑雅,甚都 」,此處的「都」為美麗之義,然而史書上卻鮮有對卓文君樣貌的描寫,當漂亮的女子成為歷史一隅的主角,書寫者往往不吝對其美貌的贊賞,或多或少會記上一筆,然而卓文君的外貌在《史記》、《漢書》等所謂信使上卻毫無記載,因而后世將相如和文君的愛情佳話神話化的傳奇小說中也鮮少有描述卓文君外貌的,想必,文君實在是相貌平平。司馬相如作為一個才華橫溢、風度翩翩的窮光蛋費盡心思地撩來其貌不揚的寡婦卓文君,可見,求財嫌疑實在極大。
《漢書》對司馬相如的評價與《史記》并無大異,且《史記》的「相如不得已,強往」在《漢書》中則改為「相如為不得已,強往」,此處的「為」通「偽」,詳裝、假裝之義,司馬相如之狡詐更顯三分。
《西京雜記》中對司馬相如的評價亦不高。楊雄在其《解嘲》中更是直斥司馬相如「 司馬長卿竊貲于卓氏,東方朔割炙于細君 」,魏晉葛洪也說「 樹塞不可以棄夷吾,奪田不可以薄蕭何,竊妻不可以廢相如,受金不可以斥陳平 」,時人及后人對司馬相如「買官」、「竊妻」頗有微言,然而隨著時代的轉換,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故事逐漸成為沖破家族門第自由戀愛的象征,司馬相如的形象也從丑化走向了美化。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的之間發生的種種事件必然是唯一性的,是「真實的歷史存在」,然而由于歷史書寫者的不同,書寫歷史的時代不同,同一真實的存在過的「歷史事件」在歷史書寫中卻發生了各種變形。
司馬遷在《史記》里對司馬相如的記載就是完全客觀和真實的嗎?司馬遷難道不是站在自己的視角,處于時代的局限,權力的脅迫,在有限的視域下有選擇性地記錄著所謂的「歷史」嗎?除了全知全能的上帝視角,這世間誰人眼中的事實能被稱為真正的事實呢?試想,同一個正方體放在兩個相對的人面前,他們看到的面會是同一面嗎?新歷史主義認為真正的歷史根本不存在,它強調主體對歷史的干預和改寫,所謂的歷史不過是話語建構的歷史。它認為歷史包含四個層次:
第一,「真實的歷史」,「真實的歷史」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復性
第二,「記錄的歷史」,記錄的歷史具有政治傾向(因而有句話說「一切歷史都是勝利者的歷史」),價值判斷(一切歷史都是當代人的歷史),邏輯鑒別,文藝修養,心理傾向,個人好惡等。
第三,「傳播的歷史」,這便涉及到丑化和神化,我想這不用我多說了吧,現代歷史在美化誰,丑化誰顯而易見。
第四,「接受的歷史」,這是「歷史」一詞的終極意義。如今我們對司馬相如的印象停留在「賦圣」以及「情圣」上,這便是接受后的歷史。所以那些未被主體接受的歷史就有可能毫無存在的意義。薩特認為歷史具有個人性、神話性與謊言性,唯一重要的歷史是個人記住的東西,而個人只會記住那些他愿意記住的東西,過去就是我們決定從中記住的東西,除了我們對它的有意記憶,過去不會有任何其他的存在形式。我們選擇未來,也以同樣的方式選擇過去。
傳統歷史學將事實看作是「給定的」,歷史具有唯一的正確性和視角的真實性,歷史事件具有連續性(新歷史主義則認為時間關系和因果關系不是一回事),歷史書寫者具有研究姿態的中立性(新歷史主義則認為中立性、客觀性完全不可能存在),在新歷史主義這里,歷史被認為發明的成分多于發現的成分,甚至發現部分也是人為建構的(視域的有限性,主體關注焦點的差異),發明成分就更不用說了。
歷史事實具有甄選性,歷史不是簡單的歷史,而總是「為........什麼的歷史」,歷史是有目的的建構的。
最后引用那句話「一切歷史是勝利者的歷史」,朱棣作為一代帝王,統治階級,便是所謂的勝利者,他手中掌握的政治權利、話語權利決定了關于他的歷史書寫。我想正史里恐怕少有其負面的歷史記載,題主所說的關于朱棣凌遲宮女等暴行也許是野史里記載,想必利害相關不大,因此無所忌諱,或許也有對朱棣的丑化行為。總之,兩種記載都無法全然信之,畢竟我們無法還原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