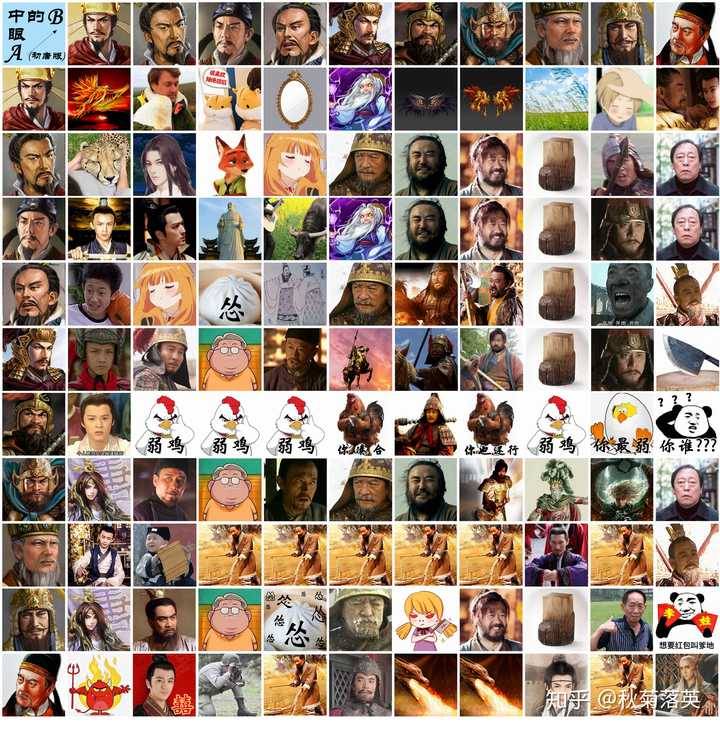『白起為秦平趙,乃被昭王所殺;亞夫定七國之亂,卒為景帝所誅;文種設策滅吳,翻遭越王所戮;伍胥竭力為國,終罹賜劍之禍:乃是君之過也,非臣之罪也。至若趙高、韓信、黥布、陳豨之儔,此則自貽厥釁,非君之濫刑也。高祖失于存功之能,光武獲于置將之妙。臣安君社稷之固,君處臣危亡之地,豈是相酬之道也!』——李世民《金鏡篇》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人君為善者,多不能堅守其事。漢高祖,泗上一亭長耳,初能拯危誅暴,以成帝業,然更延十數年,縱逸之敗,亦不可保。何以知之?孝惠為嫡嗣之重,溫恭仁孝,而高帝惑于愛姬之子,欲行廢立,【蕭何、韓信功業既高,蕭既妄系,韓亦濫黜,自余功臣黥布之輩懼而不安,至于反逆。君臣父子之間悖謬若此,豈非難保之明驗也?】朕所以不敢恃天下之安,每思危亡以自戒懼,用保其終。
」 ——《貞觀政要》
嘗侍宴慶善宮,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舊唐書·尉遲敬德傳》